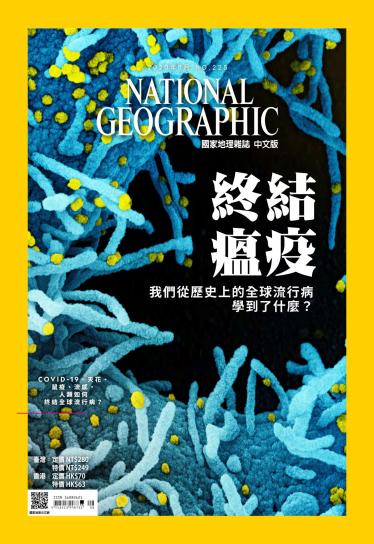▲正常的生活被打亂,各地的人因C O V I D – 1 9看不見的威脅而被迫分開。
我擔心再這麼下去,我們之中某些人將永遠無法完全走出自我隔離;恐懼和不確定性將導致我們失去部分與世界的實際連結。我的名字來自以湯瑪士小火車為主角的《鐵路系列》童書。我大哥當時在讀這套書,小西方火車頭奧利佛是他的最愛之一。我母親覺得這個名字很美,因此我是以一輛火車命名的。 我這個名字也帶點詩意:我是同卵雙胞胎,這讓我跟我哥哥伊森沿著平行的軌道發展。如果你曾認識雙胞胎,那應該聽過這些事了。我們穿一樣的衣服,髮型剪成一模一樣的閃亮黑色鍋蓋頭。我們看起來一樣,受到一樣的對待,什麼事都一起。 隨著我們的成長,我和伊森都渴望成為兩個獨立的個體。我們交不同的朋友,穿不同的衣服。中學時,我們常避不交談。接著我們選了不同的大學,在人生中第一次分開生活。 這讓我很興奮:沒有雙胞胎的生活,沒有人會把我和另一個人搞混,不再有無形的力量將我們綁在一起。但這個改變也讓我害怕。即使我把伊森推開,知道他就在那裡仍令我放心,而且他一直都在。獨自一人上大學,我感覺自己失去了一些東西。 自從正常生活被打亂, 各地的人們因COVID-19 看不見的威脅而被迫分開後,我經常回想當時分開的情景。突然間,我們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認為理所當然的面對面相處被剝奪了。我思考著這代表什麼,對於我的未來、大家的未來,以及我這個世代的未來。 我在大學主修哲學,在我最早修的一門課中,我偶然接觸到哲學家法蘭克.傑克森設計的思想實驗,一般稱為「瑪莉的房間」。假設瑪莉是一個天才科學家,她一輩子都住在一間黑白的房間裡,唯一的感官輸入來自一個黑白的電視螢幕。 瑪莉可以接觸大量資訊,了解關於色彩知覺的每件事;只是她從未親眼看到色彩。有一天,假設她走出了房間──看見藍天、摸到了樹的樹皮。傑克森的問題是:她是否能學習到任何新知?體驗世界是否會讓我們得知一些無法藉由閱讀學習到的東西? 傑克森認為可以。我們不在實體世界生活就得不到的東西,他稱之為感質,感質無所不在──在太陽、大地和其他人身上。感質是在完全虛擬的生活中缺少的事物。 多年來我一直有種揮之不去的直覺,認為幾乎所有我必須做的事都可以在線上完成。我可以在線上跟朋友說話、寫作、閱讀、報導新聞、看電視、聽課、瀏覽社群媒體。大學課程在3月下旬全部改成線上後,我能做的事情實際上更多了。我的教授在線上有空的時間變得更多。讓我分心的事減少了,我能更輕鬆地取得許多資料。 在封鎖期間,我搬回去和家人住,但我的生活跟之前差不多。我的治療師母親仍然為病患看診;我妹妹用Zoom 上中學課程。只是一切都在線上,另一個現實。 這種網路生活是我這個世代習以為常的。電腦陪伴我成長;隨著我長大,電腦變得變小、更隨手可得。我的同輩比我們的父母更早學會如何上網,弄懂如何透過文字訊息打情罵俏,透過群組聊天形成小圈子。早在疫情之前,我就會在週六夜晚獨自待在房間,讓筆電和手機螢幕的光照亮我的臉,在線上和朋友聊天,一邊看體育賽事的精采重播。 大學畢業後,我將加入愈來愈虛擬化的勞動人口。電腦正要──或即將──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取代人類,不管是金融業者、卡車司機還是工廠工人。還沒消失的許多行業正轉成線上作業。我想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將從事盯著電腦螢幕或在電話上交談的職業。身為作家,我可能最後會每天在家工作。我的生活大半已在線上度過,因此這個可能性感覺沒那麼糟糕。不過,這樣的現實還是非常奇怪。
我擔心這次疫情的經驗可能讓人相信,在實體上與他人隔絕時我們仍能過得不錯。對於許多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我們主要的擔憂並不是會感染病毒。我們更害怕的是對未來的極度不確定。有很多令人恐懼的可能性,而且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冒出來。但我認為最可怕的一種──除了這個疾病永遠不會消失以外──就是這樣普遍的虛擬生活可能也永遠不會消失。 我擔心這次疫情經驗可能讓人相信,在實體上與他人隔絕時我們仍能過得不錯。要是這種程度的與人隔絕是未來常態,會怎麼樣?在這種處境下,確實有什麼消失了。我很確定,因為當我不是透過線上而是直接經歷某些事時,我的感覺不一樣。某方面來說,分開反而讓我和伊森更加親近。我們到不同州念大學後,開始會打給對方。我不記得一開始誰先打給誰,我們從不聊心情、女生或哲學。我們只講些近況小事:「我已經24小時沒睡。」「我剛嗑了一個超大漢堡。」 我絕不會現在跟他說這個──太肉麻了──但這是真的:距離讓我們釐清自己實際上喜歡對方的什麼。因此當我們透過虛擬世界跨越橫亙於我們之間的實際距離後,我們獲得了一些什麼。 然而,另一個人的實際存在是無法虛擬的。沒有螢幕能夠取代手臂環繞在肩膀上的感覺。我擔心再這麼下去,我們之中某些人將永遠無法完全走出自我隔離;恐懼和不確定性將導致我們失去部分與世界的實際連結。失去感質。 我和伊森如今回到兒時的家中,暫時又住在一起。我們被迫待在一起──還有我母親、父親、妹妹、哥哥和他女友──就像世界上有其他地方的人被迫分開一樣。和我的雙胞胎待在一起不再困擾我了。我們熬夜打遊戲、講笑話、輕聲地大笑以免吵醒別人。感覺很好,不是自己一個人。 我們仍然很少聊嚴肅的話題。我跟伊森說到瑪莉的房間時,他聳了聳肩:「嗯,我覺得有道理。」我鬆了口氣。伊森常笑我愛講人生哲理。我會一直講一直講,相信自己是在挖掘某些深層的真理,然後他會說:「拜託這很蠢耶。」 不過我們的關係不在於我們說了什麼;而在於有所連結。這個春天,我們一起漂白了頭髮,用同一個水槽,把頭髮從黑色變成幾乎全白。我也不太曉得我們為什麼這麼做,那是伊森出的主意。我們現在看起來一樣,但也和以前不一樣。 在疫情開始幾週後一個溫暖的夜晚,我們走去家後面的火車鐵軌,試著在細細的金屬軌道上保持平衡。我總是一直失去平衡跌下去;小西方火車頭奧利佛脫軌了。 不過,伊森一次可以持續走個幾分鐘。偶爾,我們最後會走到彼此身旁,一起往前走個一時半刻。我們前方的路很黑,有點嚇人。但是某種直覺讓我們繼續下去,在平行的軌道上前進。

▲奧利佛(左二)與WPRB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