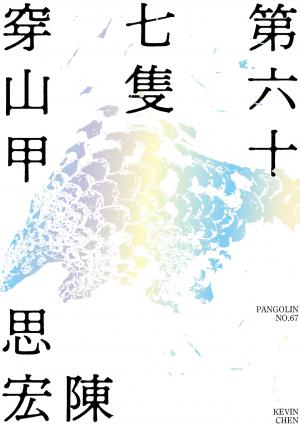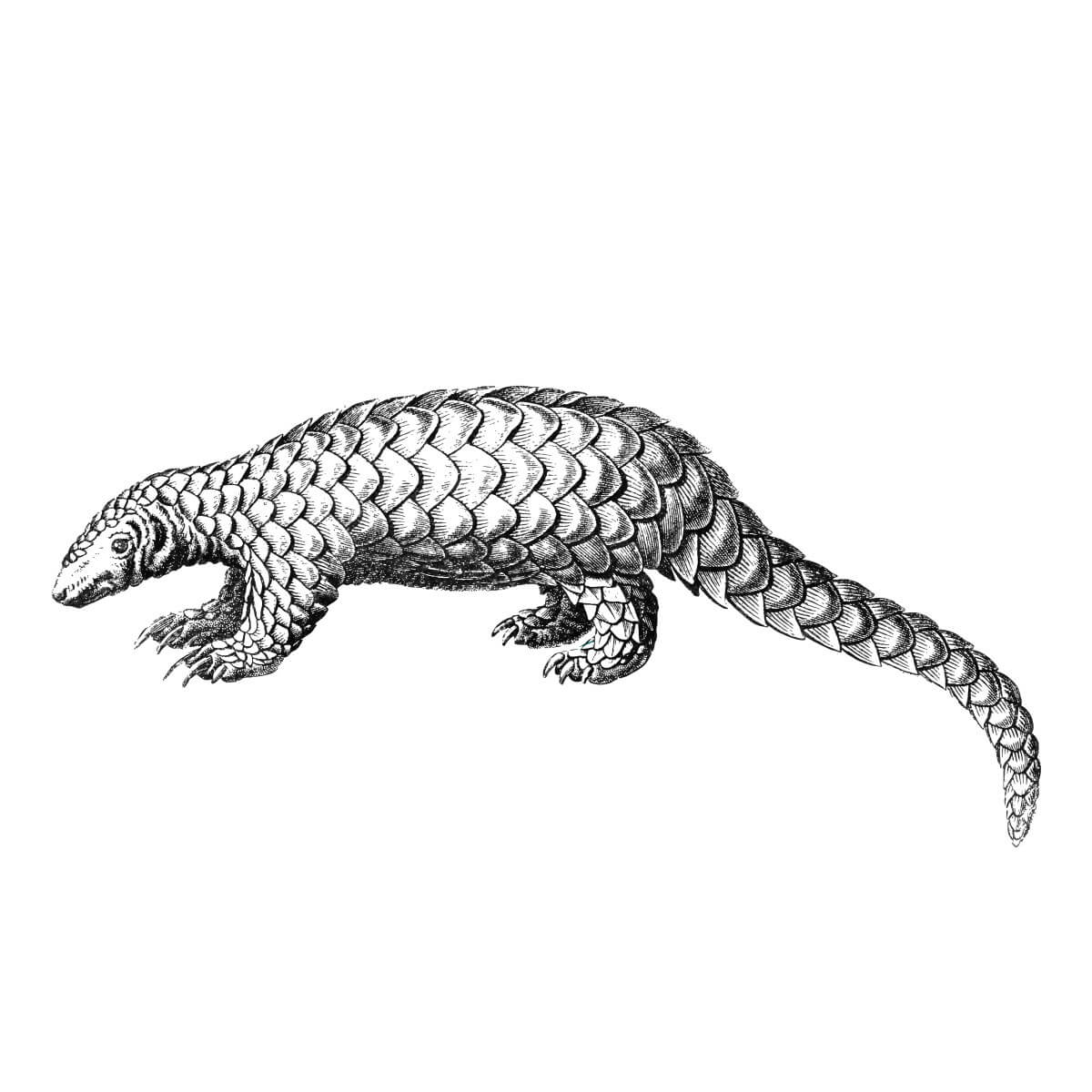
第一部 散步
1.睡覺
她和他,在巴黎夏天結束那天,終於又睡在一起。
有多久沒睡在一起了?他完全不記得,她記得。他依然是離開的那個,她知道自己是留下的那個,等著,繼續等著,沒有離開,無法離開,等自己睡著,裝睡,等失眠離開。等久了,她不太確定自己是否就是在等他,還是在等自己放棄。真的等太久了,分秒成世紀,她的等待擴張成雨林,生態物種氣候繁複,地表腐葉爛枝等真菌分解,失眠的豹等睡意,蜘蛛網上的蚊等死,貘等走失的孩子回巢,樹葉上的雨滴等墜落,蟒等脫皮,鷹等風,樹冠等日出,穿山甲等蟻。別無他法,只能繼續等,等消失的那個人爬回床上,與她一起在雨林裡沉沉睡去。就算那個人終於現身,等待就結束了嗎?或許等待就是她活下去的驅動,再等一下子,再等下一個,等待不是被動,是主動,身體備戰姿態。為了好好睡覺,她一定要等到他。
終於又在同一張床上,好久好久沒睡的她,頑石意識終於鬆動,下雨了,溪暴漲,頑石甘心離開乾涸河床,隨溪水漂流,沖刷到很遠很遠的陌生境地,不痛了,身體深處不明痛源消失了。他是大雨,他是洪水,只有他能搬運她的睡眠,把堅硬乾枯搬移到茂盛溼潤。在這張窄小的巴黎床上躺下,她清楚,這一覺始於洪荒,鼾聲喚醒文明,口水甘霖大地,醒來窗外將是銀光金光噴濺的嶄新未來。
他卻睡不著。
窗敞開,窗外巴黎也無眠,月明,鄰居鬧,街上酒鬼叫囂。
風送來雨味。他知道這味道叫做Pétrichor,查了字典,潮土油。J教他的。J和他在公園長椅上等訂單闖進手機,盛夏燥熱,午後時光滯留,只有雨,與風勾結的雨,才能修補龜裂的時間。他不介意那樣的等待時光,萬物遲到,巴黎暫停。公園樹下長椅只剩他跟J,只要陽光再囂張一點點,就差一點點,樹木摩擦就會著火,公園灰燼,這次他終於澈底消失。他每次刻意消失都好怕。但這次完全不怕消失,身旁有J。
J說什麼他都聽不太懂。口音濃重的法語。反正他也無意聽懂。聽不懂,卻懂。他寡言,就聽J說。無關文法句構發音,就是明白。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懂」。詞彙片語標點符號都理解了,就「懂」了嗎?真正想說的話是龍蝦,有硬殼有螯有觸角會夾人,趕緊沸騰一大鍋熱水,龍蝦入鍋,鍋蓋阻生路,殺死真心話就不傷人了,謊言鮮美可口。J語言熱烈,聲腔不隱匿,舌齒直白,想什麼說什麼,想親吻伸舌頭,想哭泣扯喉嚨,想尖叫身體演十集恐怖影集,不曖昧,迎面對撞,口紅只選最艷紅,假睫毛長如章魚觸手,愛到底,恨到死。所以就算聽不懂字詞,他總是懂J。
某種熟悉的味道忽然飄進公園,鼻腔裡黏稠,近似霉味。J站立深呼吸,歡呼,艷紅雙唇不斷說Pétrichor,他搖頭,不懂不懂,J在他手心拼字,Pétrichor。他在手機輸入,拼錯好幾次,終於找到,潮土油,這三個中文字他也沒聽過。植物遇旱所分泌出的油滴入泥土岩石裡,雨水撞擊乾燥大地,雨水混雜這種油所產生的氣味就是Pétrichor。他其實也聞到了,從小他就很怕這種霉味,聞到會立即想到母親,想到離別,眼睛會下雨,原來有正式科學名稱。潮土油攻城,從公園四面的街道奔騰而來,整個夏天不斷喊渴的土壤張嘴迎接。皮膚還沒攔截到雨滴,雷先擊中艾菲爾鐵塔,街上行人急奔躲雨,花裙瑪麗蓮夢露,雨聲潑猴,強風撕爛露天咖啡座的陽傘,咖啡杯蛋糕盤酒杯煙灰缸在人行道上摔成一首鏗鏘德布西,繽紛商店招牌掙脫螺釘,誰按下了時間快轉鍵,巴黎加速,暴雨即將占領這個小公園。J和他手牽手閉眼深呼吸,Pétrichor灌滿身體,雨下一秒才抵達,兩人緊貼的手心已經先下了猛烈的熱帶雨。熱雨來襲,在頭皮上鑽孔,J舌頭是土撥鼠,伸過來在他臉上打洞。
這個巴黎夏天沒有雨,也沒有J。乾旱高溫,連續好幾天高溫衝破四十度。今天她來巴黎了,就躺在他身邊。這麼久沒見了,同睡一張床,整夜枕生疏。但還能睡哪裡?睡沙發?這巴黎小公寓不到八平方公尺,沒有空間容納沙發。他們一起躺在床上,烏雲沾溼窗外月,涼風起,他清楚聞到Pétrichor,快下雨了,雨聲未到,潮土油先抵達。原本以為這巴黎夏天無止盡,是她吧,把秋天帶來巴黎了。
不是跟自己約好,夏天結束之後,他就要離開巴黎了。怎麼此刻身旁躺了她?怎麼還困在這八平方公尺的籠?
J被救護車吞掉之後,他又想消失。窄小空間沒多少衣鞋,說走就走,整個巴黎不會有人挽留他,塞納河不記得他,羅丹沉思者沒見過他,凡仙森林的草木忘了他。問題是,能去哪裡?不知道。專長是消失,缺憾是不懂找目標,總是想逃,卻從來不知道能去哪裡。當初怎麼會來巴黎?想不起來了,反正又要離開了。忽然邀請函塞入信箱,好久好久沒見的經紀人找到他,滿身爆汗走上頂樓小公寓,大聲咒罵夏天,你真的很難找,你這什麼爛地方竟然沒有電梯,樓梯髒死了,你到底在巴黎搬了幾次家?你知道我問了多少人才找到你新地址?樓下那些妓女好吵,天哪,你家是鳥籠啊。比我家浴室還小。
鳥籠比喻並不讓他覺得困頓。經紀人圓滿肚子撞上門框,進門後旋身撞倒水杯,席地坐下吁吁抱怨,汗雨橫流,肚臍幾乎貼上天花板,他才覺得這籠真是窘迫,無法待客。
經紀人說,臺北的她爽快答應了,電話上說非常開心能飛來法國。4K修復上映特別邀請你們兩個演員,導演已經過世了,很多演員都找不到,就靠你們了,另外,同一天還會播放你當年得男主角獎那部,一次兩部喔,算是個人小小回顧展。
經紀人說的是法文還是中文還是英文?似懂非懂,聽覺淤積多年,滔滔人語都是細長牙籤,從耳朵戳入腦子。經紀人嘴巴持續砍木刨木噴出銳利牙籤:「我們現在沒合約了,我這是幫你,我看你身材狀況保持不錯,有持續運動喔?我看一下手臂,很好很好,肚子呢?很好很好,要不要就利用這次機會復出?我這個人重情面,立刻幫你安排試鏡好不好?考慮一下啦,人家主辦單位很有誠意,主席很喜歡你的電影,一說到你啊,眼睛冒出星星。」
千萬牙籤塞滿他腦子,他想像人眼冒出星星的畫面。那眼睛飛出的星光是夏夜螢火蟲嗎?還是電影院忽然停電,整個大銀幕瞬間墨黑,但剛剛電影裡的爆破場面還遺留在銀幕上,視覺裡殘留的那些晶瑩光點?還是巴黎入冬第一場雪?低溫吸走城市所有聲響,忽然一切都靜默,灰暗天空飄來點點白光,抬頭迎雪,睫毛攔截初雪,在視線裡晶鑽發光?或者是流星雨?身體深處大爆炸,宇宙塵埃衝向雙瞳,燒出晶亮的箭矢光跡。他看過這樣的奇觀,母親向他道別之後,眼睛立即燒出斑斕的火流星。再見。再也不見。
透過經紀人,失聯許久的他和她連上線,加了彼此通訊軟體帳號。他其實從來沒點頭,沉默不語,經紀人就當他答應了,幾套名牌西裝快遞到他的住處,出席影展戰袍。公寓真的太小了,西裝皮鞋襯衫配件擺地上掛牆上,無容身之地,他想開窗跳出去,不是尋死,只是需要呼吸,昂貴華服太漂亮太華麗太貪婪了,吸光小公寓裡的氧氣,小桌小椅都窒息變形了。開窗,他半個身體往外探,張口把整個巴黎瑪黑區全吸進胸腔。大力吐氣,把瑪黑區吐還給巴黎。身體只要再往外幾公分,手鬆開,下墜,他也可以把身體還給巴黎。樓下窗戶忽然吐出蒼白手臂,手指夾菸,不見頭顱,窗戶噴出一大口煙霧,樓下的法國阿嬤戒菸又失敗了,菸燃盡,菸屁股朝街道扔,滿是皺紋的手心朝上,等待下一根菸從天而降。街上妓女抬頭看到他,飛吻燦笑。那飛吻力道強悍,把他推進窗戶。搬來這裡第一晚,他睡不著,到街上人行道坐著看人,醉鬼,潮人,觀光客,扒手,妓女。紅髮妓女走過來在他身旁坐下,朱紅指甲點點手機上一張電影劇照,再指他。他點頭,紅髮女說了一串他聽不懂的話,紅唇貼上他的右臉頰左臉頰,食指貼唇,噓,意思是我不會跟別人說。他想,妳可以盡量說沒關係,真的沒有幾個人認出我。後來J就完全沒認出他。他想跟J說,我以前是演員。還沒說出口,還沒來得及一起看他演的電影,J就消失了。
他和她擠窄床,從小共眠的神奇默契,翻身,反側,蜷縮,兩體完全不碰觸。並不會不舒適,氣味,鼾聲,睡姿,都是熟悉。卻也不至於安恬,畢竟這麼久沒見,有這麼多話沒說出口。J消失之前幾乎每晚都睡在這裡。J睡姿紊亂,無法靜躺,輾轉囁嚅。J把被子踢掉,說不需要被子,我就是你的被子,纖瘦人肉被子趴上他身體,如剛離水的蝦抖動。這顫抖的被子總是要哭一下才能入睡,嚎啕或者低泣,一定有淚。他緊緊抱著這被子,下體整晚堅硬,真的好想進出J的身體,但不能吵醒J,忍一下,J好不容易睡著了。
雨滴終於來敲窗,潮土油更濃郁,溫度驟降,天色銀亮,睡意釣竿終於朝他揮過來,雨聲是誘餌,他張嘴上鉤。睡眠接力賽,他終於接到她的棒子。
她醒之前最後一個夢是白色的。
她清楚夢境是什麼地方。她搖頭想甩掉那白色。為什麼一定是白色的。白牆白床白枕白地板白衣。白色根本不靜謐,死亡顏色,看了就煩。她好想干預自己的夢境,駕駛載滿油漆的卡車衝撞,紅黃綠紫,隨便,蓋掉白色就好。但一直等不到那輛卡車。白色不斷入夢。
身旁的他安靜睡著。醒著的時候不說話,睡著也無聲無鼾,全身平躺靜止,從小就這樣,完全沒變。這張床根本太小了,他粗壯的身體怎麼可能有辦法安穩入睡,膝蓋彎曲,頭腳依然抵牆。
粗。對,凝視身旁的他,她腦中就想到這個字。短髮粗,鬍子粗,嘴唇紋路粗,眼角皺紋粗,眉毛粗,脖子粗,手臂粗,手指粗,指紋粗,大腿粗,腳趾粗,雞雞粗,手肘那塊皮膚粗。她好想用手指捏那塊手肘粗皮。她的凝視停駐在他的褲擋,堅硬的粗壯下體撐開棉質寬鬆睡褲,巍峨大山,粗粗的烏黑陰毛迤邐至肚臍,像是誰用毛筆蘸墨,在這個粗粗的身體上潑墨山水。
她想走進那幅山水,卻從來找不到路徑。
好渴。
好小。
體內的湖見底,張口一定可以盈怒溪納百川。起身走兩小步就抵達廚房,喝掉一整罐水壺。這公寓真小,裝兩個人真是太擠。公寓門開太用力會撞上淋浴設備,她的大行李是肥碩大象,一窗一桌一椅一床一壺一小冰箱一洗手臺,牆上掛著新西裝,無衣櫃,兩瓷盤兩水杯,不成對的刀叉筷,小小的電爐,兩小鍋,幾件摺好的衣褲,一雙球鞋,全新亮漆皮鞋,兩個啞鈴。就這樣,清簡無塵,無裝飾,太窄太小了,連灰塵也找不到棲身之地。昨晚睡前想洗澡,他說出門買牛奶,她感激他的體貼,脫衣服總不能叫他面壁吧。淋浴設備是牆角兩片塑膠門,牆上伸出蓮蓬頭,一塊肥皂,沒地方掛毛巾。水量不能調大,蓮蓬頭不能舉高,否則牆面天花板地板雨露均霑。馬桶緊貼淋浴門,無門無隔間,她把行李放在馬桶旁,大象充當廁所門。整間公寓,比她在臺北住處的更衣室還小。
你怎麼有辦法住這麼小的地方?
她坐在地板上看窗外雨,靜靜喝水,看他的粗大下體,怎麼一直都不疲軟,他夢裡是誰支撐這粗壯?反正一定不是她。一陣涼風嬉鬧入窗,引發她體內閃電。
痛。
趕緊吞服止痛藥。
才幾個小時前,機長廣播降落,絮語艙壓在她耳裡築精緻鳥巢,雛鳥啁啾。機翼削切雲朵,機身微顫,香檳生波濤。巴黎快到了,終於。香檳配止痛藥,痛源不明,無以形容。高空亂流魚刺,在她身體裡這裡戳那裡扎,平躺痛,坐起痛,吃餐點痛,喝酒痛。十幾個小時航程痛楚堆積,喉嚨欲洪鐘,不可以,絕不能敲鐘,不能讓旁人發現。止痛藥有效,心理作用吧?藥丸一刷進身體就覺得制伏痛楚了。或許痛根本不存在。或許巴黎不存在。她根本沒搭上這班飛機。都是荒誕妄想。要是能睡著就好了。睡了,醒來一切如初。無血。無樹。無子。無語。無女。無母。無雨。回到童年那張床墊。我們一起好好睡個覺。睡醒一切歸位,重新再來。
巴黎啊巴黎,我來了,終於好好睡了一覺。
她知道,一見到他,她一定可以入睡。一定可以的。
他到底是誰?叫什麼名字?有沒有改名字?幾年沒見了?變老變胖變瘦了?有沒有伴?還拍電影嗎?記得她嗎?還願意跟她睡覺嗎?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