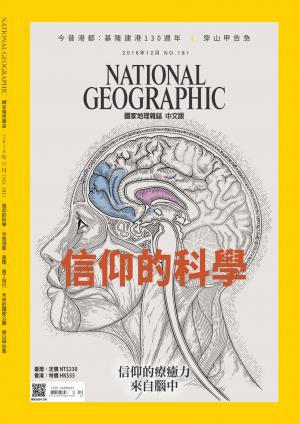當我和薩沙.馬卡列維奇在車站旁的飯店碰面時,他不知道要帶我去哪裡,於是我們就沿著下塔吉爾夏日塵土飛揚的街道隨便走走。這是烏拉爾山脈東麓一個逐漸沒落的工業城市,而這位24歲的水泥工人,金髮綁成馬尾垂在背上,牛仔外套改的背心上縫著一片邦聯旗(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方蓄奴州的戰旗),當我問起,他說:「我以為這只是代表獨立。」
我們走過一棟小小的方正平房建築,牆上布滿蘇聯國旗上的紅色星星以及橘黑相間的聖喬治絲帶圖案,那是帝國、蘇聯和俄羅斯時期的軍事勳章專用的絲帶。
薩沙聳聳肩說:「我們可以進去,不過裡面都是那些熬過九○年代的人們。」
薩沙也是熬過九○年代的人,1991年12月,就在他出生前幾個月,克里姆林宮上的蘇聯國旗降了下來、升起了俄羅斯的三色旗。原本期待俄羅斯的生活會開始跟繁榮的西方國家一樣好,但他們旋即體認到痛苦的現實:要把管制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要從一個幾百年來都是專制君主政體和極權統治的社會中生出民主,將是艱苦漫長的過程。

我從沒機會體驗九○年代的俄羅斯。我們一家在1990年4月離開莫斯科。2002年我第一次回到俄羅斯時,佛拉迪米爾.普丁總統權力正盛,大眾視他為終止九○年代動盪不安的解藥。之後,我多次返回俄羅斯,還以記者身分住了好幾年。我認識的俄國人,大部分都多多少少經歷過74年蘇聯實驗的洗禮。在這段歷史的大悲劇裡,我們對家人的小歷史小悲劇,有著深刻而個人的了解。但成長中的這一代,只認識一個飽受九○年代磨難、之後又受普丁嚴密統治的俄羅斯。今年,是蘇聯解體25年,我再次回到俄羅斯,拜訪像薩沙這樣的年輕人。我想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對生活有什麼期望?對俄羅斯又有什麼期望?
薩沙說,下塔吉爾「到處都是工廠和監獄。」這個城市曾經因為製造蘇聯的火車車廂和坦克聞名,但現在最出名的卻是閒置的工廠、失業問題,還有佛拉迪米爾.普丁。2011年,普丁宣布打算再次參選、爭取連任第三次總統,莫斯科和其他大都市都爆發了抗議活動,抗議者以年輕、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中產階級為主。那年冬天,下塔吉爾的一名工廠工人在全國性的電視節目中告訴普丁,他和其他「哥兒們」隨時可以到莫斯科痛扁這些示威者。普丁並未同意,但是這個城市從此被視為普丁支持者的大本營。
下塔吉爾現在有個新市長,是普丁派來改善市容的,但當地的生活依舊艱困。薩沙到學校學焊接,在工廠工作,薪水還不錯,直到後來油價崩盤,加上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而受西方國家制裁,經濟一落千丈,薩沙開始領不到薪水,他花了一年找工作,最後在距離兩小時車程外的一座波音工廠找到工作。現在他每月賺3萬盧布,相當於450美元,差不多是當地的平均薪資。我在薩沙下班後跟他碰面,整天工作下來,他身體疲累,雙手髒汙。
他形容的下塔吉爾,是個最好大家都一樣、否則可能引發暴力的地方,他說:「這裡的人對看起來跟他們不一樣的人很有攻擊性。」要看起來跟他們一樣,重點是當地工人階級的標準打扮:運動服、短短的三分頭,只在額前留薄薄一層瀏海。薩沙說他的同伴通常都是坐過牢的人的小孩,「他們不尊重法律。」因此薩沙學會打架,用拳頭、用刀子。有一次他打完架、身上染著其他人的鮮血走回家,當他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竟流露出奇異的幸福開心模樣。
薩沙真正的心願是逃離這裡,到國際大都市聖彼得堡開一間酒吧。他去過聖彼得堡幾次,那是他覺得最自在的地方。但他的女朋友並不想搬家,除非他在那裡買一間公寓。以他們倆的薪水來看,這個夢想可能永遠只會是夢想。
這是在下塔吉爾經常聽到的話: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夢想,但在普丁統治的俄羅斯,現實卻讓他們無法實現夢想。他們想旅行,但他們賺的是盧布,經濟危機已讓貨幣價值腰斬。有些人想創業,卻不知該如何應付地方上的貪腐狀況。他們因此把眼光放低,只想要一棟房子或公寓、一輛車、一個家。對其中許多人而言,這些他們渴望的東西,正是他們因為家人曾活過九○年代而不曾擁有的。
20歲的亞歷山大‧庫茲涅佐夫是下塔吉爾人,他告訴我:「九○年代時,我們家非常拮据,1998年爸爸拋下我們走了。」當年他才三歲,「媽媽把薪水全拿來養我,我沒有什麼玩具,家裡只有我一個人。」這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記,「對我來說,家人最重要,我不想為了追求職場高位而犧牲家庭。」 他的父親在1994年打過第一次車臣戰爭,他建議亞歷山大:「不要去當兵,兒子。」但亞歷山大並沒打算設法逃避兵役,他解釋:「我一直想從軍,我家族裡每個人都當過兵。」除此之外,軍旅生活能讓俄羅斯年輕人有機會找到比較賺錢的工作:像是當警察或到聯邦安全局(FSB,前身為蘇聯祕密警察KGB)工作。
從軍讓他能有機會像他父親一樣當警察,亞歷山大說:「我真的想要一份穩定的收入。」 我跟亞歷山大聊到一半,他的朋友史蒂芬蹦蹦跳跳地加入了我們。他給了我一個淘氣的笑容後說:「所以,你在寫關於前蘇聯狀況的報導嗎?那時候大家的生活好過多了。」 「什麼!」亞歷山大大聲抗議:「以前生活比較好?不對,才沒有!」 他們爭辯著蘇聯時期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後來,1992年出生的史蒂芬突然想到他其實有問題要問我:「你們美國人在壓迫我們,用經濟制裁教訓我們。你們打算怎麼對付我們?打仗嗎?」他解釋為什麼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普丁對抗西方都是理所當然。 史蒂芬不肯告訴我他姓什麼,因為我是美國記者,但等到我要離開時,他主動要載我一程。他說:「不過說真的,我想離開這裡。」 離開哪裡?我問。
下塔吉爾嗎? 他說:「不是,是俄羅斯。」 剛才那番愛國的慷慨陳詞之後,我可沒想到他會這麼說,為什麼?我問。他的口氣中並沒有憤恨,只是淡淡地說:「這裡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沒有機會、沒辦法成長和發展,沒有辦法發揮自己的潛力。」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女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曾寫道:「在蘇聯時期出生的人和蘇聯解體後才出生的人,並沒有共同的生命經驗,他們就像來自不同星球的人。」前蘇聯是在一片樂觀的浪潮中解體的。許多人都相信俄羅斯很快就會成為繁榮的西方式民主國家。但1991年的樂觀,卻在後續十年間往往叫人沮喪的各種矛盾中煙消雲散。計畫經濟終結之後,有一部分人晉身鉅富、或成為新興的中產階級;但其餘的人卻突然陷入貧窮。商店貨架上放滿了過去買不到的商品,但能購買這些商品的貨幣卻週期性地貶值。犯罪激增,尤其是商業犯罪。政治開始攤在陽光下,開放參與,但許多俄羅斯人卻逐漸視政治為齷齪的勾當。
俄羅斯人努力適應這種陌生的現實,這是個前所未有的自由時代,許多人卻覺得這樣的自由讓他們無所適從。莫斯科獨立民調機構「列瓦達中心」的社會學家娜塔莉亞‧佐科亞說:「當這些(西方)價值觀碰上了現實,當大眾發現改變發生得太慢,這些價值觀就漸漸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她說,年輕一代反而已開始重拾「蘇維埃社會的核心價值。」
薩沙、亞歷山大、史蒂芬和他們的同伴確實活在一個與父母和祖父母輩截然不同的星球上,不過,在某些方面,他們卻變得更蘇維埃了。這是件奇怪的事:這些年輕男女對於蘇聯時代生活的匱乏、習慣和殘酷所知無幾。普丁世代身上並沒有蘇聯時代留下的創傷。他們渴望的安定、正常生活(完整的家庭、不見得滿意但卻可靠的工作),正好反映出他們在九○年代沒有、卻在普丁時代找到的東西。 但他們非常沒有安全感,根據列瓦達中心的資料,18到24歲的俄羅斯人(也就是蘇聯解體後出生的第一代)當中,有65%只會計畫未來一到二年內的事。他們對政治也很冷感:大多數人對政府不想讓他們知道的新聞事件一無所悉,83%的人說他們不曾參與任何形式的政治或民間社會活動。 莫斯科是個看起來像倫敦與上海混合體的金融中心,市區蓋了許多玻璃帷幕大樓。我跟麗莎約在其中一棟大樓亮晶晶的白色大廳裡碰面,我跟著她穿過連接這些大樓的地下通道,裡面有咖啡館、商店,還有一個有普丁和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洛夫畫像的展覽。麗莎是時尚的年輕女性。我們點了午餐,麗莎一邊大聲喝著羅宋湯,一邊告訴我她的故事。她請我不要寫出她的姓氏,以免讓她父母不高興。 1992年,麗莎出生在俄羅斯的遠東城市海蘭泡,父親是歷史老師,1991年蘇聯解體時,麗莎的父親也曾走上莫斯科街頭歡慶民主到來。但當他在蘇聯解體後回家時,卻不得不想其他辦法養家活口,他開始越過邊界到中國跑單幫,把衣服、電器等物資帶回俄羅斯轉賣
···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