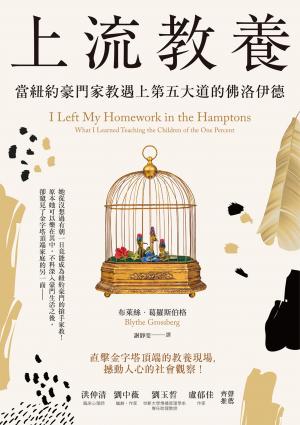我認識頭一個家教學生蘇菲時——那年她十五歲,正翩翩走下鋪著白地毯的氣派螺旋樓梯。這間位於公園大道的雙層公寓採白色裝潢色調,從沙發到粗毛地毯,到在她腳邊狺狺狂吠的迷你貴賓狗。她撈起其中一條狗要牠安靜時,私立學校制服短裙隨之翻飛。她伸手扭了扭牠小小腦袋上的蝴蝶結。當我們上樓要進行寫作課時,她的兩位菲律賓裔女管家,還問我們要吃些什麼或喝些什麼。
她的房間裡,粉紅格子床罩呼應著書桌椅子的布料,其他一切雪白無瑕,完全沒有青少年房間慣有的雜亂。她將課本整齊有序疊好,而那是唯一可見的雜物。連她的液晶電視都儲放在木頭落地櫃裡。唯一打亂空間裡白色和粉紅色系的事物,只有她蒐集的法國名瓷利摩日(Limoges)瓷盒,也全部互以直角仔細排好。她跟父親在漢普頓高爾夫聯賽的合照,裝在水晶相框裡。只有在她打開書桌上方的嵌入式櫥櫃時,才看得到大部分青少年房間會有的雜誌剪貼及朋友的照片——妝化得太濃,衣著講究,一身名牌洋裝搭高跟鞋。
她拿出《大亨小傳》,說起她的作業:撰寫一篇文章,談談蓋茲比是否實現了美國夢。她的兩條白狗又開始汪汪叫,最後,其中一個菲律賓女人過來要牠們安靜,並且抱了牠們下樓去。
她說:「我打算說蓋茲比沒有實現美國夢,因為我的老師就是那樣想。」她停頓片刻,緊張地舔舔嘴唇。「除非妳覺得我應該寫別的。」
我們來來回回思索各種構想,我可以察覺,我認為這個題目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這點讓她很緊張。反之,我請她在文本裡找出支持自己論點的段落,證明蓋茲比並未實現美國夢。她機械式翻著書頁,指甲上塗的亮片指甲油,有一半已經被她摳掉了。她讀了以下段落,關於蓋茲比喧鬧奢華的派對:
「『每週五,紐約的水果商會送五箱柳橙和檸檬過來——每週一,同樣的那些柳橙和檸檬會變成切半無肉的果皮,高高地堆成金字塔,從他的後門離開,』」
她準備往下讀,但我請她放慢速度,想想這個景象。她說:「我爸媽的廚房在派對後也是那個樣子,所有的檸檬皮都擺在吧台旁邊。在長長的夜晚過後,我媽看起來就像榨乾的檸檬。」她意識到派對客人蹂躪蓋茲比的房子,就像夏天派對賓客定期破壞她父母在漢普頓(Hampton)1的家,結果令人無力又失望。她似乎能夠理解那個段落,並且跟個人經驗產生連結。
她按響書桌旁牆壁上的對講機,要女傭送些綠茶上來,幾分鐘內,茶就送來了,以瓷杯和瓷盤盛裝,杯緣放了搖晃的檸檬薄片。我們終於擬出了大綱,我想她表現得還不錯,提出了可論辯的命題,並且從文本裡整理出證據。我離開的時候,她勉強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還是說蓋茲比實現了夢想呢?」她大聲說出疑問。
我離開時興高采烈。這次的經驗令人陶醉——綠茶、白狗、拿錢討論蓋茲比。我做夢也想不到,累積多年的閱讀、在公立高中因為熱愛詩詞被人嘲笑,最後會帶來有利可圖又能實現抱負的工作機會。
我到蘇菲家的經過相當迂迴。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時,我遇到兩個重大問題。比較簡單的一個是,在我認為佛洛伊德跟當代現實脫節以後,我摒棄佛洛伊德學派,偏好行為學派。比較困難的問題是,要能夠買得起新鞋去取代原本那雙兩邊都有洞的平底鞋,或是請窩在我布魯克林公園坡公寓大廳裡的流浪漢一杯冰咖啡——或者甚至是買杯冰咖啡給自己。要付地鐵車費也很吃力,所以我才用走的,鞋底因此磨出了洞。基本上,我發現,我的哈佛學識教育讓我遍覽群書,但並不會主動替我掙來地鐵車費。不過,這是我的錯,因為我為了攻讀心理學,繞過有利可圖的金融工作,而我丈夫也是個長春藤盟校畢業生,成了雜誌編輯。我們簡陋的公寓裡塞滿了書本。不過,我依然相信心理學會解開人類心智的謎團,從利他主義到非理性——而單是探索這些謎團,對我來說,價值已經超過六或七位數美元的收入。
我踏著磨薄的鞋底,踩過紐約的街道時,想了不少事情。我無意間想到要寫一篇以ADHD為主題的論文,等於替自己鋪路,往後可以跟有學習差異和ADHD的學生共事。我在一所提供菁英教育的曼哈頓私立學校找到一份學習專家的工作,專門協助有各種學習差異的學生,年薪五萬四千五百美元,長久以來,我頭一次覺得安心,即使家裡有個新生兒要照顧。經過數年僅供維持生活的收入之後,既然生了孩子,我判定自己需要更穩定的事物。我在紐約住了十年,到目前為止勉強過活,不曾涉足零工經濟。但當我在上東城女子學校教書的朋友問我,能不能幫一個性格甜美但壓力過大的高二生上寫作課,我簡直喜出望外,這種工作要我免費做我都願意。而能夠拿到費用——加上原本的薪水——簡直是極樂世界,幾乎無法想像。在我成長的麻州鄉間,小孩常常要我無償幫忙。
進入那棟公園大道大樓靜謐安全的大廳,等於步入一個承諾了富人的自由、擁有美術館般超然的世界,同時還有著足以讓緊張的十五歲孩子平靜下來的滿足感。我萬萬沒想到,我在研究所如此排斥的佛洛伊德正在我心中蠢蠢欲動,在那些公園大道的大樓裡,有著鮮花百合妝點的寂靜室內,各式各樣的精神官能症正等著上演。
蘇菲在一篇報告拿到她的第一個A之後,成績從平日的B+神奇地扶搖直上,我在布魯克林和曼哈頓的雙層公寓及褐石宅邸裡也變得有點炙手可熱,就像突然風行起來卻還沒被列入Zagat美食評鑑裡的餐廳。後來,我又接了更多家教學生,那些母親把我當成她們的祕密,有一位母親發現她女兒對手的母親也找上我時,相當不悅。「可是,是我們發現妳的。」她哀號。
有個名叫麗莎的母親,她是銀行家,平日會到南塔克特(Nantucket)駕帆船,她說「我們現在有布萊絲,我知道我女兒可以平安度過中學了」時,讓我不禁畏縮。她這樣宣布之後,發了電報給女兒,親愛的,妳需要最好的人選來幫忙,就是有博士學位的家教。她也寄了以下訊息給女兒:在每個狀況裡,都有必要花錢購買正確的協助,就像妳會買適合的Dooney & Bourke提包。這種心態在第五大道上相當普遍,有個學生曾經向我解釋化學考試為何沒過,「別擔心——我們要換家教了。」那個帆船手的女兒莉莉,是我所見過最甜美、脾氣最好的孩子之一。她天生就有副軟心腸,常在微積分先修測驗以及重大壁球錦標賽裡表現失常,任憑私立女校小圈圈的惡毒以及無情的壁球行程所擺布。母親希望莉莉能以奧黛麗赫本般的優雅揮拍打出壁球的切球,但莉莉的能耐其實遠勝於此。她腦袋清楚,而在她世界的許多人並不,她成了某種青少年版的維吉爾(Virgil),在壓力爆表的公園大道煉獄裡擔任我的嚮導2。當我碰到正在讀《神曲》的家教孩子時,常常想到莉莉,她引導我進入地獄的同心圓裡。我們坐下來上課的時候,她會一點一滴透露出當日的艱辛,跟我說起之前參加派對時,自己只有一半心神在場,另一半巴不得窩在自家床上看影集《辦公室風雲》(The Office)。
我驚奇地聽著她的故事,欣賞她衣櫥裡穿皺的金絲洋裝,那是她上個週末踩著細高跟鞋在曼哈頓四處趕場的結果,而我的週末時光最多就是耗在我們家轉角的刨冰攤子。我不工作的時候,通常就在家陪兒子,因為對我而言,工作的意義不只是專業的驕傲,也是為了能夠陪伴他和我丈夫。把閒暇時間拿來在紐約到處閒蕩,對我來說是個陌生的作法,我總是迷失在研究所的研究或工作中。在奇怪的資本主義計算法裡,我工作是為了待在家裡。
莉莉告訴我,家長不在家的時候,就會有人舉行轟趴,而家長常常不在家。她有朋友甚至不知道爸媽晚上人在哪裡,也有家長會在晚上十點打電話給孩子,說目前在別的城市,那天晚上趕不回來。這使得第五大道成為舉辦派對的完美地點。即使管家在場,他們為了保住工作也為了逗孩子開心,不會去跟家長打小報告說他們不在家時發生了什麼事。莉莉學校的孩子會租用由行銷公關經營、名聲可疑的俱樂部,然後向同學收取入場費。這些俱樂部無人看管。在一次家教課上,莉莉告訴我,「我去一家俱樂部參加同學辦的派對,孩子們都在屋頂上鬼混。」以她的行話來說,意思就是孩子們在屋頂上做愛。莉莉說的是真是假,我無從證實,但不無可能。第五大道上的孩子會做所有孩子做的事,只是方式更為極端。
為了參加這類型的派對,莉莉和她朋友可能必須支付高昂的入場費。他們平日有不少錢可以自由運用。在我工作的私立學校,孩子會帶著一百美元的鈔票參加自製糕餅義賣會,會帶金卡去參加戶外教學。這種狀況曾經讓我的一個學生飽受嘲笑,因為他拿父親的美國運通金卡去布魯克林的街角雜貨店買貝果。其他客人似乎覺得饒有興味,後來卻覺得憤慨,我很高興我們最後平安脫險,順利走出了那家店(結果,那家店不接受以金卡消費兩塊美元的貝果)。
莉莉和蘇菲的父母會固定提供很多零用錢給孩子,或直接把信用卡交給他們。這些就讀知名私立學校的中學生通常可以出校吃中飯,而這些學校散落在曼哈頓和布魯克林某些區域,午餐通常並不便宜。他們不常在學校食堂用餐,而是在城裡到處遊蕩,買珍珠奶茶、壽司捲和十五美元的漢堡。對這些私校生來說,一週至少花個一百美元的午餐餐費稀鬆平常,而那還不包括他們在下課時和放學後買的七美元咖啡飲品。
這些孩子年紀輕輕就已是老饕。蘇菲的解釋是:「我絕對不能去讀一間買不到好喝的卡布其諾的大學。」因為這個緣故,她沒辦法去讀紐約市或洛杉磯之外的大學。這些孩子知道怎麼分辨沙拉葉。「噢,菊苣!」在我工作的私立學校中,有個五年級生走近沙拉吧的時候叫道。我從沒想過小孩子會這麼喜歡菊苣和布里乾酪。
當然,錢也會花在其他地方。幾年前流行的是香菸,近期則是調味電子菸。當地電子菸專賣店會販售這些味道嗆鼻的油,裡面含有的神祕成分其實會讓孩子們很不舒服。電子菸最初上市的時候,青少年們合理推斷電子菸總比喝酒或一般香菸健康,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電子菸會損害年輕的肺和腦,而且依然會造成尼古丁上癮。我擔任家教課的另一個孩子崔佛,就曾經在第三大道的一家店裡偷了水菸壺和電子菸筆,只因為他說老闆賣了故障的菸筆給他,卻不肯接受退貨。
我告訴他抽電子菸對身體會造成危害,有些傷害目前甚至還無法明白,他回答說:「對啊,布萊絲!我有個朋友吸了尼古丁電子菸以後,就癲癇發作了。」我問他,這個意外會不會讓他學校的同學少碰電子菸,他說:「不會,只要走進學校廁所,就會聽到電子菸的噪音,後來我也不在意了,就跟水聲一樣普通。」
就這點而言,第五大道的年輕孩子並不孤單。全美各地的孩子都在吸電子菸(一般認為高年級生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在吸,實際上也許更多),但這些孩子也有錢做其他事情,例如賭博。崔佛的同校朋友,高年級且超過十八歲,已經開始會趁著場外賭馬的昏暗店頭關門前趕去店裡,那裡可以合法對賽馬下注,其中兩個孩子已經因為網路賭博對莊家欠下債款。這對他們而言當然無關痛癢。他們會苦惱一陣子,然後將價值八百美元的鞋子以四百美元削價售出,好付清凶惡莊家的欠款。對孩子來說,網路賭博是個愈來愈嚴重的夢魘,根據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少年賭博問題暨高風險行為國際中心估計,約有百分之四的孩童有賭博問題。網路賭博讓他們對虛擬世界的風險上了癮,而富家孩子手頭上有現金,足以讓他們陷入更深的債坑。
他們總有其他辦法在網路上燒錢。幾乎每次家教時段,莉莉都會收到高價衣物的包裹。她的管家露比來自巴貝多(Barbados)3——個性正經八百,正在攻讀大學學位——忙著拖進J.Crew和Splendid服飾品牌寄來的包裹;在跟家教一起撰寫報告和準備數學測驗之間,這些東西能為莉莉帶來短暫的快樂,而她幾乎每個科目都有家教。莉莉是個身材微胖的金髮女孩,肌膚蒼白,一雙藍眸。她的母親嬌小削瘦,大聲說她希望「壁球可以讓莉莉擺脫嬰兒肥」,然後在行事曆精確記錄,以便讓女兒的家教時段不會互相衝堂。
家教期間,莉莉會縱情撕開紙箱,展示那些充滿熱帶風情且不適宜在二月的紐約市穿上的服飾。風格過於大膽,也不適合穿去上學——像是豹紋連身裝,腋下的洞大到會露出粉紅色胸罩。她有自己的預算,可以挑自己的服飾。她偏好Comme des Garçons這個品牌,我有一陣子也喜歡上那種高筒帆布運動鞋和印了心形圖案的藍白條紋衫,直到我發現那種鞋子價格高達一百三十五美元為止(很多都要幾百美元),而一件簡單的棉衫標價超過一百五十美元,表示家教一個鐘點的費用連那件稅後的棉衫也買不起。我很快就習慣了這件事——自己身上的衣服比學校和家教的學生便宜。有個性格刻薄的七年級女生穿的衣服比我好很多,問我:「妳那件背心哪買的啊?」我心想這件背心是在某間二手店買的,反正肯定不是歌壇巨星王子(Prince)會去買覆盆子貝雷帽4的地方,於是灰頭土臉承認了這點,那件背心後來不曾再穿。
服飾通常是莉莉用來討價還價的籌碼。到了十六歲,她已經建立自己專屬的風格,而服飾通常被拿來當做獎賞。身為獨生女,她對父母經常出差的狀況並不開心。為了不讓莉莉太常抱怨,他們准許莉莉突襲母親的衣櫥,也常會從巴黎或東京帶回昂貴的服飾。她的母親擔任忙碌的主管職,休假日常常和女兒出門購物,因為那就是她放鬆的方式。莉莉會跟著母親去麥迪遜大道,在米蘭糕餅名店Sant Ambroeus的紐約分店買義式冰淇淋或酥皮糕點(長島的南漢普頓也有夏季的季節性分店)。
莉莉的媽咪麗莎,只跟她的閨蜜透露過我的名字,那些閨蜜跟她在皮拉提斯課上一起流汗,那些媽媽將我視為某種家教救世主,這點令我受寵若驚。除了我祖母之外,沒人曾經賜予我這樣的力量。當然了,有個第五大道的母親在我問她「妳住第五大道的哪一側」時,差點拒絕僱用我。她停頓的時間久到給人一種脅迫感,然後語氣尖酸地回答:「那裡只有一側。」我忘記紐約上城的高級住宅區裡,第五大道的另一側就是通往中央公園入口。為了這個城外人的失誤,我痛罵自己將近一個月,但我最後還是接到那份差事了。
得到家教差事對我來說,不只是好玩,也不只是關乎我的資歷或是我閉著眼睛也能暢談大部分的小說和歷史年代這種事。就算哪天被拖去老人公寓住上很久之後,我都還會記得德國統一的年份。我的心思就是這樣運作的。對我而言,家教工作就表示能付得起兒子的保母費,更表示終於可以蹺起雙腿而不會露出鞋底的洞…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