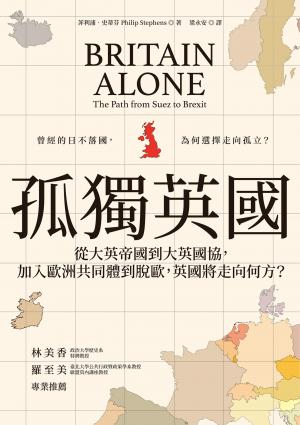「我相信香檳已經打開了,但空氣中沒有多少氣泡。」一名英國外交官在談到伊曼紐爾·吉羅路一座不知名大別墅舉行的祕密聚會時這樣說,該別墅位於巴黎西南方的郊區色佛爾。「有我所看過最亮的星星,與當前的氛圍完全不協調。」洛根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任職外交部,是個有能力、有抱負和前途看好的年輕人。在被派往巴黎近郊的維拉古布雷空軍基地然後搭乘英國皇家空軍飛機返回倫敦途中,他意識到他的任務有多鬼鬼祟祟。不過,這位英國外相的私人祕書不可能猜得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會多麼表裡不一。歷史也不會將他視為一個見證人,認為他見證了一場粉碎英國國際形象和打破她帝國夢的災難。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傍晚,洛根把一份匆促以法文打字的文件帶到唐寧街,交給首相艾登,而這份文件向後世證明了英國、法國和以色列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三個月前,埃及總統納瑟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此前,這條地中海和紅海之間的水道被英國實質控制了七十年,是英國用以通到中東和再過去地方的戰略要道。艾登決定要出兵收回運河,但此舉將會讓他垮台,也會讓英國在一個她已經無力統治的世界中迷路。
洛根的這次巴黎行是三天來的第三次。在第一次,他是陪同外相勞埃前往,去的是同一座別墅。第二次,他和法國外交部長比諾一起回倫敦。他後來回憶說,當法國代表團抵達倫敦之後,他謹慎地融入背景中,以免被在場等候的記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他第三次到別墅是和外交部助理次長迪恩一起去,會見由比諾領導的一支法國團隊和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率領的高階代表團。迪恩代表外相在後來被稱為《色佛爾協定》的文件上簽名。一星期後,以色列對西奈沙漠發起入侵,迅速向蘇伊士運河推進。幾天內,皇家空軍戰鬥機就轟炸埃及的機場,英法傘兵從天而降,在一次精心策劃的行動中奪取了蘇伊士運河。下議院一片沸騰,紐約的聯合國亦復如此。這則外交自大和政治愚蠢的故事注定成為英國戰後衰落的一個隱喻。
艾登爵士最終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入主唐寧街十號。事件的發展將會顯示,這位資質超高的政治家當了太久的候補選手。在將權力交給指定繼承人之前,邱吉爾就曾表露出懷疑的態度,之後更不只一次鄭重地對讓位一事表示反悔。固執地無視英國逐漸縮小的角色,他幻想自己可以當華府和莫斯科之間的調停人,可以確保友好的東西方關係。邱吉爾的私人祕書柯維爾在日記裡寫道:到了一九五三年冬天,艾登「飢餓的眼睛」1——這是邱吉爾的形容——已經變得「更加迫切和更加沒有耐性」。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艾登是那麼的焦急,以致當邱吉爾見過艾森豪總統一面後決定取道海路回倫敦時,他跟隨邱吉爾登上停靠在紐約的冠達郵輪「伊莉莎白女王號」。艾登向柯維爾透露,他來是為了「向邱吉爾取得交接的確定日期」。柯維爾評論說:「有夠奇怪的,兩個認識了那麼久的人竟然在這件事情上扭扭捏捏。」艾登終於得到一個日期,但邱吉爾不到一個月便再次反悔。直到翌年春天艾登才能如願。
在下議院待過三十一個年頭又當了二十四年的部長(其中三屆是當外務大臣),沒有人能夠說艾登不夠資格當首相。他才五十七歲,比八十歲的邱吉爾要年輕很多。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聲名遠播,因為戰前他站在保守黨那邊激烈反對姑息政策。稍後,他又以外務大臣的身分,陪同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見了羅斯福和史達林。溫文爾雅、自信且準備充分,這位政治家從不懷疑自己對政府最高職位的適任性。當上首相不到一個月,他便舉辦大選,以確保得到民意支持。這次選舉讓保守黨在下議院從多十七席變為多六十席。
不管多有自信和多有經驗,漫長的等待都讓他付出了代價。內閣同僚很快就注意到他變得因循守舊和喜歡搞黑箱。他所屬的階級和世代相信英國所面對的嚴峻經濟處境只是暫時現象。一九五三年六月,年輕的伊莉莎白女王舉行了充滿帝國威儀的加冕典禮。向這位新君主歡呼致敬的除了幾百萬揮舞旗幟的忠心人民之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總統和總理、埃米爾和謝赫、王子和公主。皇家空軍的專機把新聞影片載運到大西洋彼岸,好讓加拿大的廣播公司能夠同一天放映。金光閃閃的馬車,壯盛的皇家禁衛騎兵,宏偉的西敏寺——加冕典禮這些炫示的畫面喚起了英國過去的輝煌,但艾登之類的政治人物卻以為它們還是關於未來。畢竟,印度——「皇冠上的寶石」——雖然已經獨立,但米字旗仍然飄揚在世界各地幾十處英國屬地。
艾登選擇野心勃勃的麥克米倫作為外相,但幾個月後就改變主意,因為後者強烈顯示出他對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有自己的看法。他被調為財政大臣,外務大臣一職由聽話的勞埃出任,換言之,首相等於是自己當外務大臣。但他被自己的健康拖累:一次拙劣的腹部手術讓他變得虛弱,容易發燒。這一點在隔年納瑟爾於發起大膽挑戰時將變得至關重要。體現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是過去和未來的不可避免碰撞,其中包括新興阿拉伯民族主義對式微的帝國威望的挑釁、既合作又競爭的跨大西洋關係,以及一個華府透過蘇聯的挑戰所看見的世界。三股力量都對艾登不利,但決定英國道路的是這位首相。
蘇伊士運河是根據十九世紀法國外交家雷榭的願景而建造,花了十年完成。在一八六九年通行後的幾年內就成了大英帝國的一條重要動脈。當統治埃及的赫迪夫破產時,迪斯雷利馬上吃下埃及在「蘇伊士運河公司」四成四的持股。到了一八八二年,蘇伊士運河已經是那麼重要的國際水道,以致格萊斯頓決定派兵將其占領。直到一九三六年,英國才在經歷半世紀的實質占領後正式撤出埃及。即便如此,英國仍然留下幾千部隊保衛運河。直到納瑟爾宣布將運河收歸國有的幾星期前,最後一批英軍才根據協定撤離。
對於以捍衛阿拉伯世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自任的納瑟爾來說,英法擁有「蘇伊士運河公司」的所有權和管理權一事乃是不可接受,是過去的國恥的一個象徵。他是幾年前透過發動推翻國王法魯克的軍事政變上台。這段期間,他成功把自己塑造為新興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領袖,煽動人民對運河的守軍發動間歇性的游擊攻擊,又支持約旦和伊拉克的人民反對統治當地的哈希姆家族政權——他們都是英國的盟友。一九五六年七月,他在亞歷山卓對密密麻麻的群眾講話,激烈攻擊英國帝國主義,宣布將會收回運河。英國和法國的股東雖會獲得補償,自此以後從歐洲到中東的重要水道將會由埃及政府控制。對英國來說,蘇伊士運河的戰略價值是無可爭議的,艾登曾一度稱之為「大英帝國的旋轉門」。前往波斯灣和遠東的航線維持安全暢通至關重要。來自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都是要通過運河,這些石油除了供應英國,也供應歐洲很多其他地區。
當消息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傍晚送達時,首相官邸正在舉行晚宴,貴賓是伊拉克國王費薩爾和首相賽義德,在座的還有工黨領袖蓋茨克、外相勞埃和其他客人。艾登盡了最大努力撐起英國在中東的影響力——費薩爾的伊拉克,還有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是英國發起的《巴格達公約》的參與者。這是一個軍事和經濟聯盟,用以對抗蘇聯的影響力。納瑟爾選擇自外於這個聯盟,用東方對抗西方這一招來建立他的泛阿拉伯領袖形象。客人都離去後,艾登走入書房,已經等在裡面的包括了內閣大臣、法國大使和美國駐倫敦臨時代辦。首相毫不含糊地認定,如果無法拿回運河,將會「對西方列強的經濟和她們在中東的地位及影響力造成災難性後果」。
在艾登心中,國家威望與貿易和石油同樣重要。幾年前他有過一樣的判斷,當時身為外相的他在伊朗把「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後呼籲美國人發起政變,推翻伊朗領袖穆沙迪克。根據位於華府的國家安全檔案出版的一部中情局政變史所述,倫敦和華府對此有不同的動機。「美國國務院同意艾登所認為的,穆沙迪克必須下台」,但出於不同理由:「對艾登和他的政府而言,穆沙迪克的政策有損英國的威望、影響力和重要商業利益」,但美國人卻更擔心穆沙迪克會打開大門,迎接「蘇聯的宰制」。英國有另一個觀點。她的龐大和四處蔓延的帝國一直是靠一種理解維持,那就是如果她的利益受到威脅,就必須果斷採取行動。艾登擔心,納瑟爾若不受懲治,英國的阻嚇力的威信將會被動搖。
沒有人比艾登對有關蘇伊士運河的爭論更熟悉。二十年前,英國撤出埃及其他部分的協議就是艾登和新獨立的埃及政府簽訂。在一九五四年擔任邱吉爾的外相時,他也跟新的埃及政權就蘇丹的未來和英國部隊從運河地區的撤出達成協議。這個協議讓艾登付出了政治代價。很多保守黨右翼都認為他太過討好納瑟爾,而他也受到幾十個保守黨後排議員的猛烈批評——這些人都是帝國的理直氣壯捍衛者,自稱為「蘇伊士集團」,其中包括了亞莫瑞、埃諾奇.鮑威爾和麥克林等右翼的明日之星。邱吉爾簽署了協議,但毫不隱瞞他個人是站在反對分子而不是他的外相那一邊。
當納瑟爾宣布把運河收歸國有之後,艾登和其他人的分歧消散了,整個內閣都支持他。因為是財相,麥克米倫本來也許會比較謹慎。前些年,因為政府拚命想辦法增加外匯收入來支應海外駐軍,連續出現英鎊危機。財政的緊縮讓艾德禮決定放棄聯合國交付的巴勒斯坦託管任務,又逼得英國從希臘和土耳其撤軍。在一九五六年,英國的財政再次疲弱:出口不振對英鎊造成壓力,而政府的美元、黃金儲備又因為市場對英鎊的投機性攻擊而被抽乾。麥克米倫在這一年的前幾個月設法削減公共開支,向各個內閣同僚的預算開刀。只有緊縮公共支出,財政部才可望支撐英鎊對美元的匯率。在這種情況下,麥克米倫理應對昂貴的海外軍事冒險持謹慎態度。但他卻採取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在日記裡寫道:「如果納瑟爾得逞,我們就玩完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將會瞧不起我們……那有可能是英國影響力和實力的末日。」軍隊和情報首長們還有別的憂慮。三個月前,聯合情報委員會發出一份報告,警告政府要注意蘇聯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埃及業已處於一種愈來愈依賴俄羅斯的態勢……另外,埃及人逐漸習於與俄國人合作,而為了讓他們的捐助人高興,他們已經用他們的影響力去促進蘇聯對利比亞的滲透,大概也會去促進蘇聯對敘利亞、葉門、沙烏地阿拉伯和蘇丹的滲透。」
當內閣在七月二十七日聚會時,氣氛是一片同仇敵愾。內閣祕書布魯克爵士對討論的結果作了摘要。內閣同意「英國政府在必要時可以透過使用武力來逆轉埃及政府國有化『蘇伊士運河公司』的決定」。武裝部隊奉命準備「制定軍事行動計畫和時間表」。這工作落在了鄧普勒爵士的肩上。鄧普勒官拜帝國總參謀長,這個頭銜適切地道出他的老闆們還活在過去。
內閣承認英國的法律立場是脆弱的。「蘇伊士運河公司」是根據埃及法律註冊的公司,而納瑟爾已承諾將以公道價格賠償股東。運河也一直被承認是埃及的領土,所以英國需要一個藉口。內閣決定把理據放在蘇伊士運河是一條國際水道的地位上;這種地位曾經在一八八八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約》得到公認。艾登問同僚,如果法國和美國有異議,英國是不是應該準備好單獨行動。他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失去蘇伊士運河將會無可避免導致我們在中東的所有利益和資產一項接著一項失去。」
那一天,艾登在一封私人信中尋求艾森豪的支持。信的一開始這樣說:「我們都同意,我們負擔不起任由納瑟爾無視國際協議,以這種方式奪得運河的控制權。如果我們在這件事上採取堅定立場,將會得到所有海上強國的支持。我們深信,不這樣做的話,我們和你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將會不可挽回地動搖。」十八年前,艾登因為反對姑息政策而辭去外務大臣的職位——當希特勒揮軍進入萊茵非軍事區的時候,艾登沒有說話,但張伯倫拒絕阻止墨索里尼在地中海和東非的野心卻是太超過了。兩年後,張伯倫的政府垮台,艾登加入邱吉爾的戰時內閣。所以,到了如今,姑息政策的危險已經不可磨滅地烙印在他的世界觀裡。他提醒艾森豪納瑟爾和墨索里尼的相似之處。「我倆都不能忘記,在墨索里尼最終被處理以前,他消耗了我們多少生命和財寶。所以,趕走納瑟爾和在埃及扶持一個對西方較不具敵意的政權,必然在我們的目標中具有優先地位…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