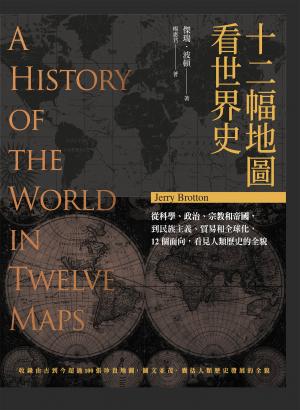埃及,亞歷山卓,約公元一五○年
古典時代的旅人從東方渡海航向亞歷山卓,最早在地平線上看到的是巨大的石砌法羅斯燈塔(tower of Pharos),座落在亞歷山卓港入口的一個小島上。埃及的海岸線基本上沒什麼地物,這座一百多公尺高的燈塔就成了水手的地標。在白天,塔尖上的一面鏡子向水手召喚,晚上便點起火,指引領航員進港靠岸。但法羅斯燈塔不只是一座導航的地標。它是向旅人宣告,他們即將抵達古代世界的一個大城市。亞歷山大大帝在公元前三三四年建立了亞歷山卓城,以自己的名字為城市命名。亞歷山大死後,托勒密王朝(托勒密原是亞歷山大手下的一名將軍)定都亞歷山卓,統治埃及長達三百多年,並將希臘的觀念與文化傳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和中東。1在公元前三世紀,旅人經過石造的法羅斯燈塔,進入港口之後,發現眼前城市的規劃宛如一件斗篷,亦即亞歷山大及麾下大軍所穿的長方形羊毛披風,是希臘軍事力量的指標性形象。希臘號稱是古典世界的「肚臍」(umbilicus),亞歷山卓就如同當時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完全籠罩在希臘的影響力之下。是把希臘城邦移植到埃及土壤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這個城市的崛起代表古典世界政治地理學一次關鍵性的變遷。亞歷山大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把希臘世界從一群孤立的希臘小城邦變成一連串的帝國王朝,版圖擴及整個地中海沿岸和亞洲。像托勒密王朝這樣把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帝國內部,戰爭、科技、科學、貿易、藝術和文化自然隨之改變。使人們以全新的方式互動、做生意、交換理念及互相學習。公元前大約三三○到三○年之間,希臘化世界從雅典延伸到印度,不斷發展,亞歷山卓就在世界的中心。西邊有來自地中海沿岸各大港口及城市的商人和貿易業者,有的甚至遠從西西里和南義前來,同時亞歷山卓和日益強盛的羅馬有貿易往來,因而致富。北方的雅典和希臘城邦,帶來深遠的文化影響。東方波斯各大王國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為南方肥沃的尼羅河三角洲,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遼闊的貿易路線和古代帝國,注入了源源不絕的財富。2
如同大多數位於民族、帝國和貿易交會點的大城市,亞歷山卓也成為學識和學術的重鎮。在西方的想像裡,亞歷山卓諸多偉大的建築地標中,影響力最大的莫過於當地的古代圖書館。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三○○年左右創立的亞歷山卓圖書館,是歷史上最早的公共圖書館之一,目的是蒐羅每一部用希臘文書寫的手抄本,以及譯自其他古代語言的著作,尤其是希伯來文。圖書館藏書上萬本,以莎草紙卷書寫,全部編成目錄,供人查詢。托勒密王朝在皇宮網絡的正中央建立了一座「Mouseion」,也就是博物館,原本要用來祭祀九位繆斯女神,但托勒密家族把這裡重新界定為朝拜學識和學術繆斯的神殿。博物館邀請學者前來研究,提供住宿、俸祿,最大的優點是能隨時進入圖書館。當代最偉大的幾位學者,從希臘各地被引誘前來博物館及圖書館工作。偉大的數學家歐幾里德(Euclid,約325-265 BC)來自雅典,詩人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約310-240 BC)和天文學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約275-195 BC)都是利比亞人;身兼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工程師身分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約287-212 BC)則來自敘拉古(Syracuse)。
亞歷山卓圖書館是最早把古代世界的知識進行系統化收集、分類和編目的單位之一。托勒密王朝下令,凡是進入亞歷山卓的書都必須交給官方,並由圖書館的抄寫員謄寫(雖然書本的主人有時只拿回一份原書的抄本)。由於古典時代的資料彼此的說法嚴重矛盾,因此無從估計館內究竟有多少藏書,不過就算保守估計也超過十萬本。一位古典文化的評注者已經懶得計算。「有關藏書的數量和圖書館的興建,」他寫道:「既然完全出自人的記憶,還有什麼談論的必要?」3這所圖書館其實是個龐大的倉庫,把古典世界的集體記憶保留在館內編目的書籍裡。套一句科學史的說法,這是一個「計算中心」,一個掌握資源的機構,負責蒐集和處理各門學科五花八門的資訊,無論「圖表、目錄或發展軌跡,普遍都能就近取得,隨意結合」,學者可以從中綜合出相關資訊,以尋求更全面、更普遍的真理。4
這裡是全球計算與知識的核心重鎮之一,也是現代製圖術的誕生地。公元一五○年左右,天文學家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寫了一篇論文,標題是Geōgraphikē hyphēgēsis,也就是「地理學指南」,後來被簡稱為《地理學》(Geography)。坐在昔日宏偉圖書館的廢墟裡,托勒密編纂了一部典籍,號稱是描述已知的世界,也為日後兩千年的地圖製作下了定義。《地理學》以希臘文在八卷莎草紙上寫成,扼要說明希臘人一千年來對人居世界之大小、形狀和範圍的想法。托勒密把自己作為地理學家的任務定義為「純粹只考慮在已知世界更廣泛、普遍的輪廓中與之相關的事物,藉此展現作為單一而連續之實體的已知世界,及其本質與所在位置」,他列出的相關事物包括「海灣、大城市、比較顯著的民族和河川,以及每一種比較醒目的事物。」他的方法很簡單:「首先必須調查地球的形狀、大小以及與周遭環境的相對位置,這樣就可能論及地球已知的部分,以及其大小和樣貌」,還有「每個地方位於天球的哪些平行圈下方」。5依據上述調查而寫成的《地理學》同時具備多重角色:歐、亞、非洲八千多個地點的經度和緯度的地形紀錄;說明天文學在地理學當中的角色;地球及區域地圖製作的詳細數學指南;也是一篇對西方地理學傳統賦予一個永恆地理學定義的論文——簡而言之,是古代世界構想出的一套完整的製圖工具箱。6
在托勒密之前或以後,沒有任何一部典籍曾經如此全面地介紹地球,並說明如何描述地球。托勒密的《地理學》完成後,足足消失了千年之久。托勒密當時的原始抄本俱已失傳,直到十三世紀才重新出現在拜占庭,而書中附帶的地圖由拜占庭抄寫員繪製,顯然是以托勒密對地球及書中八千個地點的位置所做的描述為基礎,展示出他在公元二世紀的亞歷山卓所看到的古典世界。地中海、歐洲、北非、中東和亞洲某些地區,看起來一個比一個眼熟。托勒密不知道的南北美洲和澳洲、非洲南部和遠東皆付之闕如,太平洋和大部分的大西洋亦然。印度洋被畫成一片大湖,非洲的南部繞過地圖的下半部,銜接到馬來西亞半島以東的亞洲,臆測的程度也越來越高。儘管如此,這是一幅我們好像看得懂的地圖:北方位於頂端,有幾個標示出關鍵區域的地名,同時以經緯網格建構。如同自柏拉圖以降的大多數希臘前輩,托勒密知道地球是圓的,並且用這個網格來處理把球狀地球投影於平面的困難。他承認,繪製一幅長方形地圖,必須用經緯網格「才能和地球的樣貌相似,因此在拉平的表面上用網格畫出的間隔,也必須盡可能和真實的間隔比例相稱。」7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我們不禁想把托勒密的《地理學》視為現代製圖的開山祖師。可惜事情沒那麼簡單。《地理學》內附的地圖是不是托勒密親筆繪製,學術界對此仍是各說各話:許多史學家認為,一直到十三世紀的拜占庭抄本出現,他這部著作才首度出現地圖。不同於醫學之類的科目,希臘地理學沒有所謂的領域或「學派」。實際上,沒有任何史料記載地圖在古典希臘的實際用途,當然也無從證明托勒密的論著曾被當作地圖使用。
想透過托勒密的傳記來瞭解他這本書的重要性,也是白費力氣。我們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他沒有留下自傳、雕像,甚至沒有同時代的人寫下的隻字片語。至於托勒密其他的科學論文,許多迄今不見蹤跡。即便是《地理學》本身,也流散到羅馬帝國淪亡後趁勢興起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社群。從早期的拜占庭手抄本,幾乎無從判斷內容和托勒密的原著相差多少。我們對托勒密僅有的一絲瞭解,純粹是基於他留下來的科學著作,以及多年以後拜占庭對他模糊描述的資料。從托勒密這個姓氏看來,他恐怕是在托勒密埃及土生土長,在他的一生中,埃及已經被羅馬帝國統治。儘管沒有確切證據,「托勒密」也顯示他的祖先是希臘人。「克勞狄烏斯」這個名字表示他擁有羅馬公民身分,可能是克勞狄烏斯皇帝(Emperor Claudius)對他先人的賞賜。他最早的科學研究所登載的天文學觀察,顯示他在哈德良(Hadrian)、馬可.奧里略(Marcus Aurelius)等皇帝統治期間飛黃騰達,可以推估他生於公元一○○年左右,並且最晚在公元一七○年逝世。8對於托勒密的生平,我們只掌握了這些資料。
托勒密《地理學》的創造,在某些方面顯得矛盾。儘管該書堪稱製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著作,然而依前文所述,誰也不清楚這本書是否內附地圖。作者本身是數學家兼天文學家,從未以地理學家自居,而他的生平更是一片空白。雖然他住在晚期希臘學術的大城市,不過當時希臘學術的權威和影響力已日趨衰落。羅馬在公元前三○年推翻托勒密王朝,刻意讓一度偉大的圖書館漸漸衰敗凋零。但托勒密很幸運。唯有當希臘化世界開始慢慢地由盛轉衰,他這本書才能水到渠成,奠定地理學和製圖術的定義;非要等到希臘化世界跌入谷底,才有可能描繪它的地理構造。如果說亞歷山卓圖書館曾經匯聚「人類的記憶」,爾後又遺失不見,托勒密的《地理學》就是再現了人類世界一個重要部分的回憶。但若非作者吸收了希臘在文學、哲學和科學領域上對天與地將近千年的思辨,這樣一部著作是斷然無法完成的。
雖然古希臘找不到「geography」這個字,至少從公元前三世紀起,早期希臘人就把我們口中的地圖稱為pinax。另一個常用的說法是periodos gēs,字面意思是「環繞地球之行」(這個用語成為日後許多地理學論文的基礎)。雖然這兩個用語最終被拉丁文的mappa取代,後來古典希臘對地理學的陳述——由名詞gē(地球)和動詞graphein(畫或寫)9複合而成——卻流傳後世,亙古不移。這兩個用語都透露出希臘人處理地圖和地理學的方式。pinax是一種刻有圖像或文字的實體媒介,而periodos gēs意味著身體的活動。特別是以繞圈圈的方式「繞行」地球。geo-graphy的字源也顯示它既是一種視覺(圖畫)活動,也是一種語言(書寫)陳述。儘管從公元前三世紀起,這幾個用語的使用越見頻繁,卻仍然隸屬於希臘學術中比較受到認可的學門,也就是神話(mythos)、史學(historia)或自然科學(physiologia)。
希臘地理學發展伊始,就是出自對世界之起源與創造所做的哲學和科學思辨,而非基於任何具體的實際需求。自詡為地理學家的希臘史學家斯特拉波(Strabo,約64 BC-AD 21),在耶穌誕生時,他正在撰寫十七冊巨著《地理學》(Geography),回顧何謂世界的起源,他認為「地理的科學」是「哲學家關心的問題」。斯特拉波認為,實踐地理學所需要的知識,完全掌握在「研究人類和神祇的人手中。」。10對希臘人而言,地圖和地理都隸屬於一門更大的學問,亦即對萬物秩序的思辨型研究:以文字和視覺來說明宇宙的起源和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
有關我們所謂的希臘地理學,最早的陳述出現在一部詩篇裡,詩人是斯特拉波心目中的「第一位地理學家」:荷馬(Homer)。他的史詩《伊里亞德》(Iliad)通常被認定是公元前八世紀的作品,在第十八卷的結尾,希臘人和特洛伊人的戰爭進入最高潮,希臘戰士阿基里斯(Achilles)的母親塞蒂斯(Thetis)請求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為她兒子打造一副盔甲,讓阿基里斯穿上之後和特洛伊的對手海克特(Hector)對決。荷馬描述赫淮斯托斯為阿基里斯打造那面「巨大雄偉的盾牌」,就是文學界最早的ekphrasis(對藝術品的生動描繪)範例之一。但也可以視之為一幅宇宙論的「地圖」,或是希臘地理學家所謂的kosmou mimēma,也就是「世界的圖像」,11對希臘世界的一種道德與象徵性描繪,這一幅世界圖像由五層同心圓構成。正中央是「地、天、海、生生不息的太陽和月盈,以及綴滿天空的耀眼星群」。再往外看,盾牌描繪著「兩座凡人的美好城市」,一個安享和平,一個陷入戰火;農業生活展現的是犁田、收割和採葡萄;「直角牛」、「白毛綿羊」的放牧世界;最後是「浩瀚大洋河,沿著堅固盾牌的邊緣流動。」12

▲圖1 阿基里斯的盾牌,青銅鑄造,John Flaxman設計,一八二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