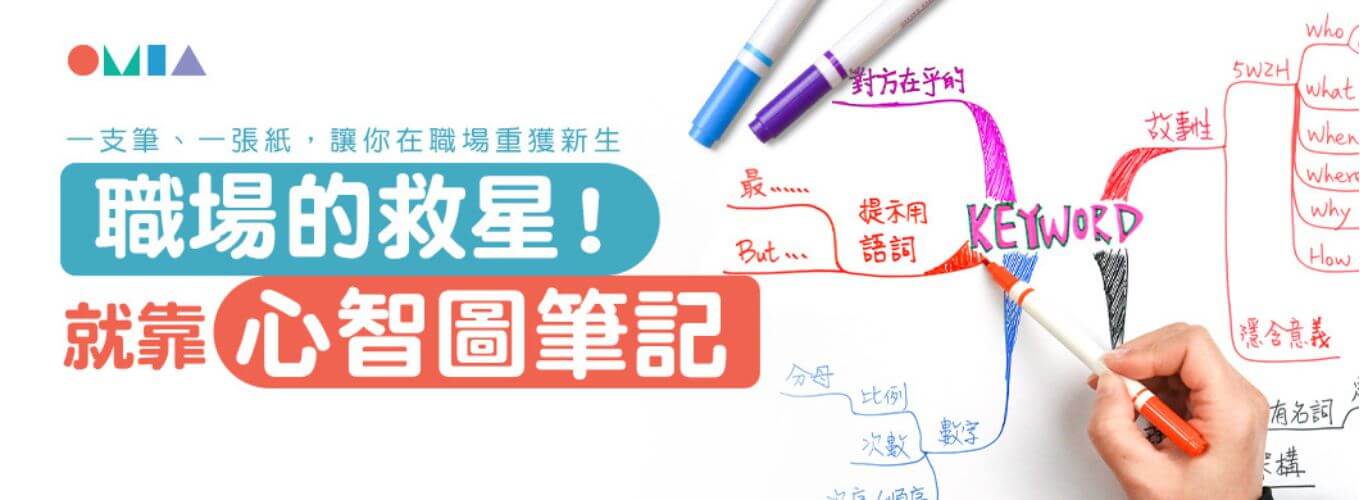因為有拍紀錄片,有機會到偏鄉教學,最明顯的狀況就是小孩子一直在減少,學校不再聘任專任教師,改以代課老師來維持教學狀況,但是等到學生人數一減少,代課老師就會被裁掉。我看到一些小學校長,通常都是分校主任,他們很努力地要維持老師跟學生的比例,我看到他們對教育的熱誠,很有想法的年輕人一直在考教甄,甚至有那種很優秀的老師,其實考了八次,我蠻驚訝的,考八次意味著每次只差零點幾分,這個零點幾分判斷適不適合當老師,表示競爭真的太激烈了。

主要角色的階級背景為何?
當時我有個出發點是想要談所謂人跟人的距離,人跟人的不能彼此了解,所以設定了一對兄弟,這對兄弟對於人生的看法上出發點就有點不一樣。哥哥代表很多像我這一輩的,所謂沒有背景、沒有家世、沒有財富,想要憑藉自己的力量翻身,這其實是我們社會裡很普遍的一種想法,就是「力爭上游」,哥哥代表了這樣的人,事實上在我這一輩,有這樣想法的人,容易做的事情是當老師,尤其過去有公費這件事情,現在其實公費的比例少很多了,但是這個翻身的途徑,非常明顯在台灣來講就是當老師,所以設定了這樣一個背景。
弟弟呈現的是,大家也會說台灣也有一些人非常樂天,他們基本上蠻接受自己的現況,所以我對弟弟的設定,就是他對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能力,有一種自在或者接受,也是憑著自己的勞動,可以好好的過生活,所以他接受做一個藍領的狀態,可是整個社會的改變,在經歷了整個大結構不穩定的狀況下,面臨了比如說小工廠的不穩定,老闆甚至有時候會付不出薪水,所以他的困境也不只是他個人的困境,其實是整個結構的狀態。我覺得哥哥想要力爭上游得到一個穩定的教職,可是卻未能夠如他所願,一直徘徊在代課老師這個工作,這其實都是一個大結構的狀況,所以這兩個角色,雖然也有很個別的狀態,也希望呈現一種普遍的代表性。
班上小朋友演技非常自然、真實,當初的選角過程為何?
一開始就是把台南、高雄所有人數少於六十人的偏鄉小學都列出來,接著一個個去看,現在有些學校在視覺效果上會非常華麗,所以我們決定去視覺上看起來最樸素的,因為我們希望他有一種普遍的代表性,希望真的是有生活在其中的,因為對我們來講生活在其中的小朋友是整個故事最重要的背景,還有包括這個老師為什麼一直想要留在這個學校,學校的氛圍應該是,讓老師覺得確實能伸展抱負的地方。 所以在這樣子的考量之下,我們做了很多的田野,最後縮小到四、五個學校,跟這些學校的校長、主任溝通後,帶幾個不同的表演老師,在周末時辦了表演課程的小營隊,透過這樣的觀察,發現阿蓮國小峰山分校這群小朋友,做為演員的條件是蠻好的,就是進入角色的創造跟想像力,還有包括身體的即時的反應,肌肉所有的協調,聽指令行動的能力,這些都加總來做一個觀察,最後選了峰山分校。這群小朋友從幼稚園就同班到五年級,同班了八年,這樣的默契真的非常好,他們像家人一樣,除了有一位小朋友是從台北透過試鏡,有電視電影的表演經驗的小朋友中選出的,把他帶下去,定位成一個轉學生的角色。
在確定是峰山分校以後,在學期中時再次帶表演老師去做小營隊,也讓藍葦華去那裏幾天的時間,跟小朋友一起上課、參加校外教學,到暑假開始有表演營,除了我們兩位非常專業的表演老師,教導約一周的課程,另外就是小黎、志宇,還有我們音樂的作曲者都親自下去帶他們唱歌,也有足球的課程,他們本來足球就踢得很好,只是就把我們的小朋友放進去跟他們做足球上的互動,增加熟識度。
電影涵蓋多項議題,包括隔代教育、城鄉差距、少子化、社會底層等,導演最想呈現是哪部分呢?
我自己覺得以故事來講,確實在呈現所謂「問題」,但是解答其實在觀眾的心中,所以電影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叫做「觀眾的參與」,對於觀眾的參與,那個故事需要跟他自己有所關聯,對我一個作者也是一樣的,就是說這故事或許每個角色都是我自己,這些所謂社會結構的狀態所產生的一些問題,最後還是回歸到我個人要面對跟承受。所以我關心的,或許是一個人在社會結構當中如何自處,如果有覺察到在某些層面上,真的是所謂結構性的受害者,也覺察到我們可能一不小心,一點一點的,慢慢地變成所謂結構性的加害者,那我們要怎麼堅持住自己,要如何在這個社會生存立足,我們心中的尺度、原則又怎麼樣去面對這些考驗,我想我比較期待的是,每一個觀眾在中間看到自己所面臨的問題。

電影在揭露一些平常很容易被忽略的東西,不管是文學電影或者美術,我們總是希望能夠把一些沒有被看清楚的,或者我們期待觀眾看到的東西再放大、揭露出來,所以選擇一個略帶距離的,非主流的敘事,它看起來有些事情好像沒有完全的揭露,其實對我而言,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可能也蠻重要的。
首先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知道我要訴諸的是一般白領的觀眾,我要觀眾跟著我的主角走,所以這個角色我希望是觀眾能夠認同的,或者能夠投射的,所以基本上設定了一個白領的老師角色,我想他在我們的社會裡,是一個比較容易被認同的角色,因為他代表著我們一般人,一般白領比較有的價值觀,帶著某一種正直,對自己或者對別人有某些比較高標準的要求的狀態。
可是我也覺得需要提醒觀眾說,即便身為這樣一個努力的人物,我們對很多事情的覺知,也並不是全面的,我們會有很多看不到的面向,所以我覺得在那個趨勢中,某一些小小的斷裂、模糊,或者是跳躍,是必要的,我們很早在寫劇本的時候,就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設定是跟著主角走,但如果我們要去透寫一些結構上的狀態,就是說讓觀眾更看到,所謂他身處在結構裡面的不得不,不自覺的偏離了他自己的核心,那我們確實需要比主角再出來一點點,所以這就是最後形成到,看起來雖然是跟著主角走,可是有某一些小小的片刻,我們似乎站的稍微遠一點點,比主角看到多一點點,在這個敘事的過程中,有這樣的企圖。
並且,這個結局是不是大家都沒有得到一點解脫、解決,對我來講,能夠覺知問題、悲傷,或許就是一個希望的開始,因為更多的時候我們不覺知,也沒有感到悲傷,那真的就是一個比較灰色的結局了。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