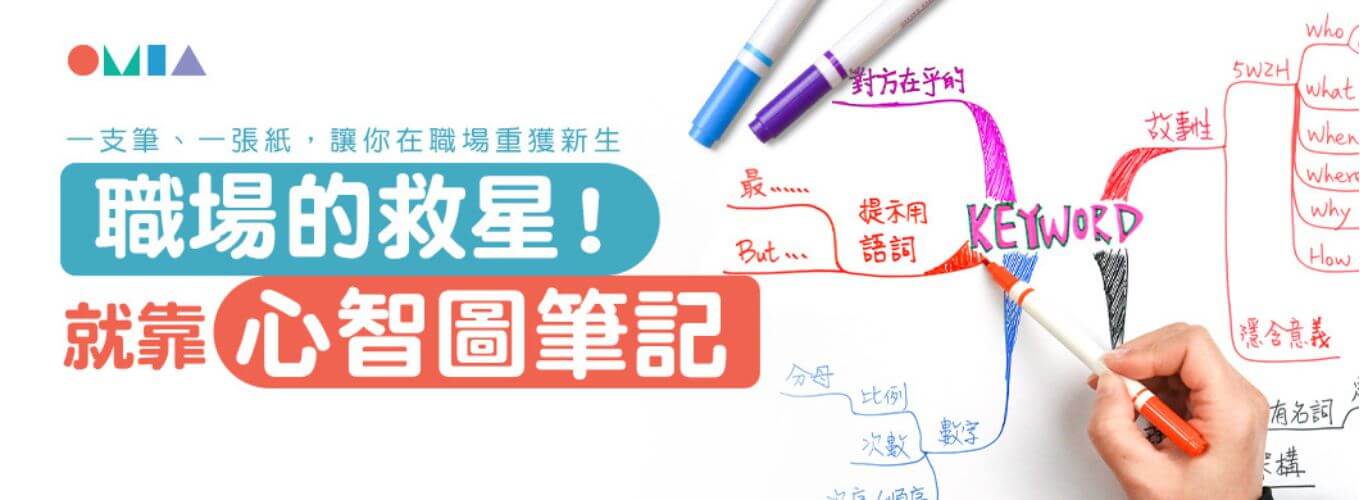以筆墨寫自由,八十二歲的書法傳道家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大廳,正高掛董陽孜的作品。她是第一位在該館大廳展覽的亞洲藝術家,更是書法文化的傳道者。 文—李若雯 「哎唷,我沒晚到吧?」一頭銀色卷髮,身材嬌小的董陽孜,人未至,聲先聞。 她自然是沒晚到的,只因這位將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的國際藝術家是出名準時,跟董老師相約的人,常得比她更早到。她確實分秒必爭。八十二歲的她,這輩子都為了書法賣命,彷彿就算能讓世人多用毛筆寫一個字都好。 「是挑戰,挑戰更要接受,」挑戰是董陽孜最常使用的詞彙,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策展人馬唯中邀請下,她為大都會創作兩件360×725.6 公分的巨幅作品,堂堂高掛於大都會入口大廳,博物館每日往來數萬名遊客,一進大廳第一印象,便是她墨色淋漓的遒勁鉅作。

董陽孜
出生/1942年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美國麻州大學藝術碩士 榮譽/行政院文化獎、中華民國二等景星勳章 著名題字/「雲門舞集」識別字體、白先勇《孽子》、《台北人》、龍應台《野火集》、齊柏林《看見台灣》、蔡明亮《臉》等作品封面題字。
而這兩幅字,一幅寫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董陽孜自己的座右銘,擺在博物館中,亦象徵館內珍稀彙集,值得細品借鏡;另幅則是「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不得不止」,來自蘇軾對創作過程的形容,董陽孜亦深有所感。 要讓美國聽到她的聲音,過程可不容易。去年七月接到邀約後,董陽孜殫精竭慮,一路寫到今年六月。董陽孜素以大字著名,然手寫大字絕非易事。她向來在家創作,脖子圍著條毛巾,佇起一管訂製的巨型毛筆彎腰揮毫。因字大、紙張所吸水分也多,一邊寫字藝術家還得一邊吸墨,董陽孜性子又急,覺得要指導助理費時,總自己包辦創作大小事,待紙上墨乾了,她早已滿頭大汗。 現實的是,同樣要費盡全力寫大字,六十歲和八十歲,狀態已截然不同。數年前她曾大病一場,住院三個月,自言是「靠機器在生活」,坦言如今每寫完一幅字便要休息良久,才能奮力繼續。 「我想她晚年有這麼一個機會,而且在這麼一個場所,對她來說當然意義重大了,」自董陽孜中學時期便認識她的作家白先勇觀察,這段時間董陽孜出奇謹慎、緊張,畢竟這是世界性的展覽,「我想華人世界應該很重視這件事。」
書法是一生的信仰 董陽孜出生於一九四二年,自幼被父親要求日日練字,念北一女時便得到許多全國性書法獎項,師大美術系畢業後,更遠赴美國麻州大學攻讀藝術碩士,後即於紐約雜誌社做美術設計,還拿了全美創作設計展封面設計獎,但她心中始終記掛書法,在美工作五年後毅然返台,「我從美國回來,我母親第一句話是,妳回來幹嘛?妳又不會打字!」 原來,董陽孜的母親思想新穎,很早就給董陽孜灌輸女性要自立、不能靠男人等觀念,更希望董陽孜畢業後久留美國發展。 但董陽孜知道自己的天命,自美返台,她知道書法需要改革,絕不能再墨守成規。「我要做『當代藝術』,我是從紐約回來的,我不能原地踏步,還是寫老祖宗的明朝、清朝的字,」她回憶。 懷抱鴻鵠之志,她埋頭寫、拚命寫,一九八○年,董陽孜在「春之藝廊」展覽,就此一展成名。 她顛覆了書法的固有形式。以往書法內容往往以長句、古文、對聯為主,董陽孜則改以簡潔俐落的大字直接點出主題;在形式上,傳統書法由右至左,由上至下,以卷軸呈現,董陽孜雖仍遵守右至左、上至下的順序,但卻打散字句結構,將文字以三角形、方形不規則排列,更捨棄卷軸,將作品如畫作般直接裱框,使其更適合做為現代家居擺飾。 她的展覽轟動藝界,書法大家、文學家臺靜農更特別著文盛讚,稱董陽孜書法有「陽剛之美」,融合書畫所長,甚至還親筆揮毫,模仿董陽孜手筆寫下「雲鶴游天,羣鴻戲海」八字,並特別標明是「擬董陽孜書」贈與董陽孜,對她評價至高。 能得臺靜農盛讚贈字,在當年簡直是如獲冠冕了。「我拿了,我就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半世紀前的往事,董陽孜回憶起來仍舊激動,「我不敢拿,我真的不敢拿,最後送給台大圖書館。」

▲董陽孜在大都會展出的巨幅作品,左為「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不得不止」,右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TheMet /The Great Hall Commission提供)
談到過往貴人,八十二歲的董陽孜彷彿又變回當時羞澀的女青年,憶起葉嘉瑩當年也常給她鼓勵,稱董陽孜是她學生,「說實話我不能算她學生哪!做學生都不配!」逾百歲的葉嘉瑩住在安養院不見客、不接電話,讓董陽孜好生掛念,她好想告訴葉嘉瑩大都會的事,「我一直在猶豫,是不是透過人告訴她,讓她知道,我沒有辜負她,」她感性說。(編按:葉嘉瑩於十一月二十四日過世) 她確實沒辜負誰。在生活中,即使你不識董陽孜,也勢必看過她的字。從台北車站大廳高掛的「台北車站」四個大字,到機場的出入境戳章、金石堂書店招牌,再到紀錄片《看見台灣》、電影《一代宗師》海報,都能看到董陽孜標誌性十足的字體。 都說「字如其人」,董陽孜的字,跟她外顯性格一般直率、痛快、敢怒敢言,不識她本人的人,若只見她雄厚壯闊的字,再加上她中性的名字,往往誤以為她是男性,而董陽孜本人,對於用性別分類各人身分十分敏感,她最不喜歡被稱為「女性藝術家」,「難道女的出來妳就要受一點(特別)待遇嗎?」她鏗鏘地說。 但有趣的是,董陽孜長期又自稱「家庭主婦」,每天在家早起做飯再練字,對這稱號她十分樂於接受,甚至有點感恩之情,「你想我自己在從來沒幹過一天工作,我居然就在家裡養活了兩個小傢伙(指兩個女兒),」她說,「是不是,不容易吧?」 宣紙上獨舞,為使命感創作但比起要兼顧家庭與創作,難上千萬倍的卻是力挽書法衰微的狂瀾,她這輩子可說是看著寫書法的人愈來愈少,更讓她痛心的是,如今連學校也不教書法了。這或許解釋了董陽孜為何年過八旬,創作能量仍源源不竭,她太急了,即使明知單靠自己奮力宛如蚍蜉撼樹,她仍使盡全身每一簇力量,只為讓書法更接近大眾一點。 她很有行動力,近二十年,董陽孜開始頻繁「跨界」,讓書法與現代舞、爵士樂,甚至與服裝設計結合。她更努力衝出台灣,二○二一年,亞洲首間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香港M+開幕,當時馬唯中在該舘任策展人,便請她為該館創作五件大型書法作品,釘在博物館大廳兩根巨柱四面上,十分搶眼,英國《衛報》即稱董陽孜為「讓書法變酷的藝術家」(theartist making calligraphy cool)。 「她很有意思,她做事情是往前的,她是絕對沒有退後的,而且說到做到,」對於相交一甲子的好友,白先勇如此評價。 或許是始終專注看向書法的未來,對於過往,她很果斷。她素來不喜拍照,六十歲那年,更將所有的照片、信件都燒毀,只保留與摯親的合照,「留這些照片感覺是給晚輩負擔,你想爸爸媽媽照片這麼多怎麼辦?爸媽的朋友一個都不認得,」董陽孜認真地說,「幹嘛給人家負擔呢。」 她還要繼續向前走,大都會展出後,她早已規劃好二○二六年的展覽,看來沒打算休息,「要閒著我能幹嘛?我也不會每天打牌,也不跟朋友出去玩,妳能幹嘛啊?當然做藝術創作,」她又滔滔不絕地談起她下一回的書法復興計劃,眉飛色舞。 有使命感的人,從來不敢老。
閱讀完整內容本文摘錄自
董陽孜 展進大都會
天下雜誌
2024/12月 第812期
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