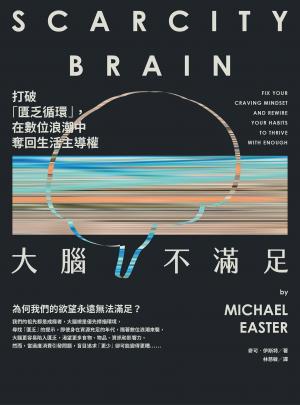早在伊拉克之前,我的旅程就從我的家鄉拉斯維加斯開始了。這個城鎮對匱乏的大腦來說,就像梵蒂岡對天主教的意義一樣。很少地方比這裡更能把現代的消費能力濃縮到一個地點。
但在這個城市所提供的一切事物當中,沒有什麼東西能像吃角子老虎機那樣觸發匱乏的大腦。拉斯維加斯不是建立在贏家身上,而是建立在旋轉的滾輪之上,這些滾輪被裝在叮噹作響、閃爍的機殼裡,人們一遍又一遍地玩這些機器——最終對自己造成傷害,這也解釋了那些機器無所不在的原因。
一點也不奇怪的是,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的賭場是座吃角子老虎機的巨大迷宮,但它也存在於加油站、雜貨店、酒吧、餐廳與機場登機口。人們一天到晚都在玩這些吃角子老虎機,一次玩好幾個小時。他們早上六點就在雜貨店裡玩,午餐與晚餐時間就在當地餐館玩。有一次我還看見一名男子緊貼著7-Eleven裡的吃角子老虎機,叫外送披薩來吃。
我問店員那是否正常。「你在開玩笑嗎?」他說。「我們還有常客呢。」
但是,拉斯維加斯並非唯一經常出現不正常人士的地方。有三十四個州允許設置吃角子老虎機,就像內華達州,許多州允許在賭場以外的地方設置這些機器——在各種日常生活的角落與縫隙中。無論我們把吃角子老虎機放在哪裡,它們都是我們的搖錢樹。
光是在美國,這個機器每年就賺了超過三百億美元,大約是每個美國人每年一百美元,比我們花在電影、書籍與音樂的費用總和還要多。而這個數字每年還會上升約一○%。
我想知道為什麼。這些機器為何如此特別令人著迷?想像一下:某個週二早上八點,你因為在雜貨店玩一台名為「Kitty Glitter」的吃角子老虎機,玩到沉迷其中,結果讓容易腐壞的東西爛掉了。
我從打電話給少數研究賭博上癮問題的研究人員開始。
這是一條死路,死得很徹底。
那些研究者控訴賭場利用奇怪、近乎顛覆性的方法來引導我們賭得更多。我們可能都聽過其中一些方法。例如,一名科學家告訴我,賭場把時鐘移開,好讓我們在賭博時失去時間感。另一位有著博士學位的反賭博研究者告訴我:「賭場絕不會有九十度的直角。」理由是直角據說會迫使我們啟動大腦負責理性、決策的部位。「直角會使你認清自己是個做決定的人,可能放慢你在機器上賭博的速度。」那位研究人員這麼說。還有另一位研究者解釋,賭場吃角子老虎機播放的音樂只有令人愉悅的C大調,據說能令我們放鬆心情,從而放鬆我們的錢包。這些主張甚至曾廣受《大西洋》(Atlantic)雜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等媒體的報導。
但沒有一件事是合理的。
只要有一點常識以及拜訪幾次賭場,便可證明這些主張要不是迷思,就是標準的商業慣例。例如,賭場確實不會在每一面牆上都掛時鐘,但像是你家當地的好市多(Costco)、梅西百貨(Macy’s)或家得寶(Home Depot)也不會這麼做。我猜想,大多數企業不會到處掛時鐘,是因為人類都會戴手錶,也有自己的手機。
而當我造訪幾家拉斯維加斯最賺錢的賭場,我發現到處都有直角。我說的是到處。拜託!吃角子老虎機的螢幕就是正方形。賭場的某些區域看來彷彿就是立體派設計師設計的。
我甚至聯絡彼得・井上(Peter Inouye),他是位吃角子老虎機的音樂作曲家。「我可以確定我並不總是用C大調。」他告訴我。他會用各種音調來寫吃角子老虎機的音樂。
但最神祕的是另一件不合理的事。大多數這些關於賭場用來吸引我們去玩吃角子老虎機的「顛覆性詭計」的迷思,至少從一九六○年代就開始廣為流傳。但那時吃角子老虎機還不普遍,加油站或超市不但沒有吃角子老虎機,連賭場的樓層都很少看見它們。
然後,大約在一九八○年,吃角子老虎機就像病毒一樣四處傳播,征服了所有賭場,並從賺很少錢到占賭場年收入的八五%。
或許那是拜我在賭場裡看見的所有直角所賜,但我有了一個理性的領悟。與其和希望我們所有人都停止賭博的人談話,我反而需要去跟希望我們開始賭博的人談談。我必須去做總是帶領記者找到最佳答案的事,必須跟著金錢走。
這使得我來到離我家只有十五分鐘路程的一家奇特的賭場。
那是城裡最新也最尖端的賭場,擁有賭博業所能提供的最迷人的吃角子老虎機、最豪華的賭桌、最舒適的旅館房間,以及最棒的餐廳。
但重點是:大多數賭場會想盡辦法來讓你進門,但在這一家——就像一間巴格達的警察局——你卻不受歡迎。
黑火新創公司(Black Fire Innovation)像個巨大的魔術方塊般,矗立在靠近拉斯維加斯莫哈韋沙漠(Mojave Desert)的邊緣地帶。這座建築物占地十一萬平方呎(約三千坪)、有四層樓,都是方形窗戶,線條簡潔現代。離空曠沙漠的紅色岩石與仙人掌只有幾分鐘路程,但這塊野地被開墾成鋪面道路,從那裡,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市中心。
從羅伯特・里皮(Robert Rippee)辦公室的寬闊玻璃窗,我可以看見拉斯維加斯大道。沙漠陽光無情的光線從賭場度假村照射出來,消費的大教堂都裝飾著霓虹燈,排列在四・二哩(約六・八公里)的拉斯維加斯大道上。
里皮坐在書桌旁,背挺得很直。博士學位證書掛在辦公室牆上。但這名男子並不像我所期待的呆頭呆腦、徒具博士資格的學究。透明的設計師鏡架掛在他臉上,手腕上纏繞著佛教徒的佛珠,他有一副鐵人三項運動員的體格,留著修剪得完美無瑕的花白鬍鬚,穿著剪裁合身的衣服。
如此複雜精緻的氣質,是他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最大也最賺錢的賭場之一擔任執行長的那些年所培養出來的。這份工作需要分析人類行為的資料,然後做出改變數百萬名訪客行動的決定。他在五十多歲的時候轉向學術界,正式研究這個主題。里皮想深刻了解使我們去做某件事的原因。
在我們會面的半世紀前,里皮正在與凱薩集團的一位執行長共進午餐。凱薩集團是世界最大的賭場企業之一,在全美國擁有超過五十個大型賭場,賭徒每年會在那裡花掉一百億美元。這位執行長當時正在抱怨一個特定的問題。
凱薩集團正在購買各種新科技,他們被告知這些新科技能提高盈利。例如,一種具備新的類似電視遊樂器特色的吃角子老虎機,將使人們被迫玩得更久。或是一種由人工智慧驅動的數據追蹤器,能根據個別客人如何下注、喝飲料與購物,創造出詳細的人物側寫,然後生成引導他們在賭場花更多錢的提示。
但是凱薩集團在花費數百萬美元使用這些新科技之前,不會知道它們是否有效。這有點像是凱薩集團自己的賭博,而在這種情況下,莊家正在輸錢。
里皮提議,要是凱薩集團與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UNLV)合作呢?那是里皮與其他科學家團隊研究科技如何影響賭場裡人類行為的地方。內華達大學與其各種研究部門,就像哈佛遇上劍橋再遇上五十一區註1,為的是影響拉斯維加斯大道及其他地區的人類決策。
他們知道什麼有效,而那些與幾何或音符沒什麼關係。
假如他們打造一個賭場實驗室呢?假如他們建造一座賭場,但完全用於研究呢?打造一個真正的賭場,但裡面充滿的是一群博士、傑出的科技人才與研究參與者。那可能成為一個測試遊戲,以及人們在得到明確的與下意識的提示之後,會如何下注的地方。或是調查對吃角子老虎機做最細微的調整,會如何觸發我們去做一件事。它可以成為一個孵化器,擁有下一個偉大創意的人們可以在這裡合作、尋找創投資金,並接觸傑出科學家和業內人士的思想。
結果就是這個地方,黑火新創公司,某種賭場的模糊區域。
「我們是個模擬拉斯維加斯大道上賭場度假村的巨大實驗室。」里皮說道。「我們可以在這裡探索新科技、行為的改變,以及更多。我們已模擬過完全整合的賭場度假村,從飯店房間到食物與飲料、娛樂、賭博,甚至零售店與招牌。」
里皮一邊告訴我、一邊走出辦公室,再走進實際上已是座賭場的區域,唯一不同的是,沒有人抽菸,以及有更多科學設備與擁有高學歷的人。
「這個區域是模擬一座體育博彩站。」他說。多樣的投注窗口與售票機沿著牆壁排列,深灰色軟墊皮椅面對著一個跟信用卡一樣薄的巨大螢幕,上面正在轉播一場明尼蘇達雙城隊對紐約洋基隊的比賽。在它兩側是較小的螢幕,上面滾動顯示的是當天的體育賭注賠率。休士頓太空人隊贏德州遊騎兵隊的賠率是負一九○,波士頓紅襪隊贏西雅圖水手隊的賠率是負一二五,紐約大都會隊贏聖路易紅雀隊的賠率是一比一。
接著我們走向一排有綠色毛氈鋪面、用深色硬木與皮革包裹住的桌子。黑色與紅色的豪華皮椅圍繞著桌子。「這些是傳統的桌上賭博遊戲,我們在這裡可以測試新的遊戲、科技,並追蹤玩家的行為。」他說道。
然後里皮指向一部圓形的機器,周圍擺放著六張椅子,一個大螢幕從它的中間升起。「我們也有電子桌上遊戲。」他說道。在那些遊戲中,參與研究的賭客在各自的螢幕下注,同時一名虛擬發牌員在中央較大的螢幕上洗牌或轉動輪盤。你最好相信人工智慧革命在賭博遊戲產業中並未被忽略。
里皮隨後指向房間遠處角落的一條走廊。走廊盡頭有兩扇左右並排的門,每一扇門都有一個鑰匙卡入口。「那會通往兩間飯店房間。」他說。附近是一個大型開放式廚房。越過廚房,是一座雞尾酒吧,接著是咖啡吧。在那些地方,研究人員可以測試賭場的房間、食物與飲料的每一個細節是如何回饋到客人的整體體驗中。
導覽繼續進行。他指向被電視螢幕占滿的牆面,上面全都在播放著測試廣告,然後指向一面互動式的智慧鏡子,那是設計用來指引賭客到達賭場裡的重要據點,接著再指向「一個為科技實驗提供的數位休息室,」他說。「再過去是一座電競體育館。」
「所以整體的概念,」里皮告訴我。「是可以把一小群人帶進來,讓他們接觸不同的情境,然後回頭去衡量他們的期待與行為,從中獲得一些行為如何隨著科技進步而改變的見解。」
「這一切都是可能的,」他繼續說道,「有七十三家以上的公司與我們合作,提供資金或設備。」凱薩集團是主要的合作夥伴。但像是奧多比(Adobe)、英特爾(Intel)、樂金(LG)、惠普(Hewlett-Packard)、松下電器(Panasonic)、Zoom、波伊德博彩公司(Boyd Gaming)與數位體育娛樂遊戲公司 DraftKings 等科技與遊戲巨頭也投入財務上的協助。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已不再像以前那樣由黑幫經營,如今成了生活研究實驗室與測試場所,是龐大的人類行為數據銀行。這就是為什麼在建商把破爛的賭桌與輪盤帶入這個地方之前,他們就安裝了它的大腦:一部有超級運算能力的數據主機。里皮朝它點頭示意。
那部主機位於一個有空調的玻璃房間,大小相當於四台冰箱。它發出嗡嗡聲,彷彿在呼吸。五顏六色的電線從中伸出來,它們全都被綁在一起,像血管一樣爬上牆面,最終消失在天花板中。
就像遍及拉斯維加斯賭場中的數據主機,在這裡的這部主機將觸角悄悄地延伸到每一個事件中。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事,不再只留在拉斯維加斯。每一個人類行為及其隨之而來的連鎖反應都聚集到雲端,在那裡被干涉、刺激與過度分析。
接著里皮帶我去看這個地方的最後一個特色,是我來這裡想要了解的事,一部用來了解人類行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經久耐用的機器。一個代表人類新時代的隱喻,在其中我們被推向快速重複的行為,一次又一次。對於其中的原因,我們可能都尚未完全了解。
「這裡就是吃角子老虎機,」他說。這些機器靠著一面牆擺放,鉻黃色的機殼閃閃發光,螢幕全都暫停。「但我想讓你跟另一個人聊聊,」里皮說道。「他的名字叫丹尼爾・薩爾(Daniel Sahl)。」
正在改變人類的不再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石油大亨,也不是一九八○年代的華爾街富豪。
他們是像薩爾這樣的人,數學型的人,同時又是「了解什麼會吸引人」的人,他這麼說道。薩爾身穿牛仔褲與運動夾克,裡面是一件印有電影《玩具總動員》(Toy Story)中「披薩星球」標誌的T恤。他的頭髮看起來該剪了。在他經過吃角子老虎機與撲克牌、骰子與輪盤賭桌,穿越實驗室朝我走來時,跟我都沒有任何眼神上的接觸。
要了解我們為何會如此深刻又快速地被推向「更多」,必須了解匱乏循環的機制。而沒有什麼比弄清楚大約在一九八○年左右發生在吃角子老虎機行業的一個特殊轉變來得更好的方法了,那件事放大了匱乏循環,並讓它成為主流,也把我帶到了遊戲創新中心(Center for Gaming Innovation)…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