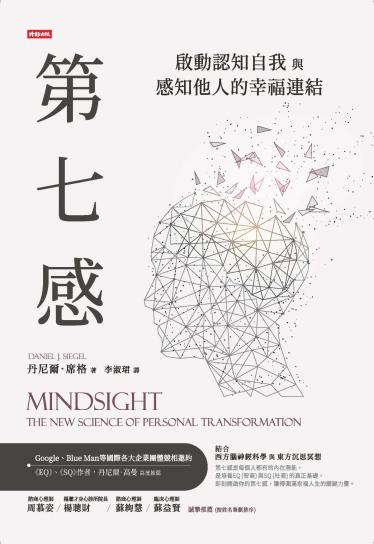壞掉的大腦,失去的靈魂:身心健康的的三角支柱
如果不是七歲大的琳娜再也不肯在學校裡開口講話,芭芭拉一家人或許永遠不會前來尋求心理治療。琳娜是芭芭拉的第二個孩子,琳娜上面有十四歲的姊姊艾美,下面則是三歲的弟弟湯米。他們在母親差點因車禍喪生時,都受到很大的打擊,但是琳娜直到芭芭拉出院,也從復健中心返家之後,琳娜才開始變得「選擇性沉默」。現在她拒絕跟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說話,也不和我說話。

接下來這對母女在草坪上轉圈圈,踢起黃色與乾枯的棕色秋葉。這對舞者接著舞近攝影機,噘起嘴唇對著鏡頭送出飛吻,然後大聲歡笑。當時五歲大的琳娜用盡所有力氣大喊:「爸爸,生日快樂!」而她父親跟著生命中摯愛的女人們一同歡笑,使得鏡頭搖晃起來。在背景裡,琳娜的小弟弟湯米在娃娃車中酣睡,他被包裹在一條毯子裡,周圍環繞著絨毛玩具。琳娜的姊姊艾美則在一旁專心地看書。
「以前我們住在波士頓時,我媽媽就是那個樣子。」琳娜突然開口說話,微笑瞬間從她臉上消失。那是她第一次直接對我說話,但是感覺更像是我從旁偷聽到她和自己說話。琳娜為什麼不肯講話呢?
那次生日慶祝已是兩年前的事了,隨後這家人搬到洛杉磯也已經一年半了,而芭芭拉因為那次正面對撞的車禍而嚴重腦傷也已經過了一年。芭芭拉那天開著他們的老福特野馬汽車去附近的商店幫孩子買牛奶時並沒有繫安全帶。那個酒醉駕車的司機筆直朝她衝過來時,她的額頭被強大的撞擊力壓入方向盤中。她在車禍後昏迷了好幾個星期。
芭芭拉從昏迷中清醒後,出現了巨大的改變。我在錄影帶中看到了過去那個性情溫暖慈愛,與人親近的芭芭拉。但是現在班恩告訴我,她「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人了」。她的身體是救回來了,但是他們以前認識的那個芭芭拉卻消失了。
與琳娜下週的晤談之前,我要求單獨和她父母談話。很顯然芭芭拉跟班恩以往的親近關係,現在已經變得充滿壓力而顯得疏離。班恩對芭芭拉很有耐心、很溫柔,也似乎很關心她,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絕望。而芭芭拉在我們談話時只是茫然盯著別處,眼神不跟我們任何人接觸,似乎也對我們的談話興致缺缺。她額頭的損傷經過了整型手術修補,即使她的肢體動作仍有些遲緩笨拙,但就外表而言,她與錄影帶裡的模樣其實很相似。只是,她的內在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
我好奇芭芭拉對重獲新生有何感受,於是問她自己認為有什麼差別。我永遠忘不了她的回答:「嗯,如果一定要用文字形容的話,我想我會說,我是失去了我的靈魂。」
班恩跟我坐在那裡,驚愕不已。稍後我鎮定下來,問芭芭拉失去靈魂是什麼感覺。
「我不知道除了這麼說之外我還能怎麼描述,」她口氣平淡地說,「其實我覺得還好,沒什麼差別。我是說,就是這樣。只是空空的。都還好。」我們接著改談有關於照顧孩子的實際問題,然後這次晤談就結束了。

芭芭拉可能復原到什麼程度,其實還不清楚。由於車禍才過了一年,許多神經還是很可能修復的。受傷後的大腦仍可能恢復功能,甚至可能長出新的神經元,製造出新的神經連結,但是當損傷範圍很大時,要恢復這些損毀的神經結構過去所支持的複雜能力與個人特質,恐怕就很困難了。
所謂的「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指的是我們的腦可以因應新的經驗,創造出新的神經連結,並長出新的神經元。並非只有年輕時才具有神經可塑性,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人們終其一生都能有神經可塑性。芭芭拉會需要復健的幫助,運用神經可塑性來長出新的連結,才能重新獲得過去的心理運作功能。但是我們必須等一段時間,讓時間跟復健發揮療癒的效果,才能得知她的神經狀態能復原到何種程度。
而我眼前的工作是要幫助琳娜跟她的家人瞭解為什麼一個活生生而外表又跟以前一模一樣的人,她的心智狀態會變得如此不同。班恩稍早曾告訴我,他不知道要怎麼幫助孩子們面對芭芭拉的改變,而他自己也幾乎毫無所知。班恩現在父兼母職,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子的起居,代替芭芭拉完成她已無法做到的事。這個母親曾經喜歡親自縫製萬聖節的服裝、烘焙情人節小蛋糕。但現在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看電視,或在社區裡閒晃。她可以走到雜貨店,但是即使手上拿著購物清單,她還是經常空手回家。艾美跟琳娜不介意她一再地煮同樣的簡單晚餐,但是她們會很氣她忘記她們特別的要求,例如她們想要的,或在學校裡需要用到的東西。她彷彿根本沒聽進孩子們說的話。
我們的治療晤談持續進行,但芭芭拉通常都只是安靜地坐著,即使她跟我單獨晤談時也一樣,而她的語言能力其實完好無損。偶爾她會因為班恩說了一句無心的話而突然變得很激動,可能因為湯米坐立難安,或琳娜用手指玩弄馬尾,而向他們大吼。她甚至會在沉默後突然爆發,彷彿是被某種內在的不明狀態所驅使。不過大多數時候,她的表情都是凍結的,是空洞而非憂鬱,是茫然而非哀傷。她顯得冷漠而疏離,我也注意到她從來不曾自發地碰觸她的先生或小孩。有一次,三歲的湯米爬到她的大腿上,她曾短暫地將手放在他腿上,彷彿是在重複以前的某個行為模式,但是那手勢裡的溫暖已經消失了。
當母親不在場時,這幾個孩子告訴我他們的感受。「反正她就是不像以前那樣關心我們了,」琳娜說。「她也都不再問任何關於我們的事,」艾美難過又生氣地補充:「她根本是徹底的自私。她再也不想跟任何人說話。」湯米則一直沉默著,緊靠著父親哭喪著臉坐著。
失去所愛是言語難以形容的。與失落搏鬥,與絕望掙扎,都讓我們充滿精神上和身體實際上的痛楚。事實上,我們腦中處理身體疼痛的部位,跟處理人際斷絕與排拒的神經中心,兩者是有部分重疊的。喪失所愛,真的會將我們撕裂。
唯有當你開始接受失落之後所取而代之的東西,你才可能藉由哀悼放下你所失去的一切。如果我們持續執著於熟悉的事物、過往的期望,就可能一直被困在失望、困惑跟憤怒的感覺裡。但是班恩跟這些孩子們要放下的究竟是什麼?芭芭拉還有可能恢復過去與他人的連結嗎?這一家人要如何學會接受一個身體還活著,但是個性跟「靈魂」──至少是他們過去所熟知的靈魂──已經消失的人?
「你地圖」與「我地圖」
我所接受的正式訓練──不論是在醫學院、小兒科或精神科──都無法幫助我處理我此時在治療室中所面對的問題。我上過大腦解剖學以及大腦與行為的課程,但我與芭芭拉的家庭晤談,是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而當時幾乎沒有什麼研究論及如何將大腦這個領域的知識帶進臨床的精神治療中。為了要對芭芭拉的家人解釋她的狀況,我只能遠道前往醫學圖書館,翻遍有關她受創腦部區域的新近臨床與科學文獻。
芭芭拉的腦部掃描顯示她前額正後方的區域受到嚴重的創傷,傷口循著方向盤的上半弧線形成。我發現這個區域負責支持我們人格中一些相當重要的功能,此外它也負責連結腦部各個分隔的區域──這是我們腦部高度整合的區域。
額頭正後方的區域屬於腦部額葉皮質的一部分,也是腦部最外層的部位。額葉跟大多數的複雜思考與計劃有關。這個部位的活動會啟動神經元的運作模式,讓我們形成神經表徵(neural representation),就像「地圖」一般,描繪出我們所處世界的各個層面。這一連串神經活動所勾勒出的地圖,協助我們製造內心的圖像。例如,當我們接收到樹上一隻小鳥身體反射出的光線時,我們的眼睛就會傳送訊號給大腦,而大腦中的神經元就會以特定模式啟動,讓我們可以勾勒出小鳥的影像。
除此之外,神經元啟動時的物理特質,還會經由我們目前還正在釐清的方式,幫助我們創造出主觀經驗──例如看見那隻鳥所引發的思緒、感受與聯想等。那隻鳥的影像可能會讓我們感受到某些特定的情緒;聽到或記起牠的叫聲,甚至會聯想到一首有關大自然、希望、自由與和平的歌。這些表徵越是抽象、越是具象徵性,就越是由位在上層的神經系統所產生,也更靠近皮質前方。
前額葉皮質──也就是芭芭拉的腦部額葉中受傷最嚴重的部分──會創造出複雜的表徵,讓我們得以在當下形成概念,或思考過去的經驗,或計劃跟描繪未來的意像。前額葉皮質同時也負責製造可描繪我們心智本身的神經表徵。我把這些描繪出內在心智世界的表徵稱為「第七感地圖」,而我也已經區分出好幾種不同的第七感地圖。
大腦會描繪我稱為「我地圖」的表徵,讓我們洞悉自己的內心,也會描繪出「你地圖」,而讓我們洞悉別人的內心。我們似乎也會描繪「我們地圖」,代表我們與別人的關係。缺少了這類地圖,我們就無法認知自己或別人的內心。舉例來說,如果沒有「我地圖」,我們就可能被自己的思緒壓倒,或被自己的感覺淹沒。而缺少「你地圖」,我們就只能看見別人的行為──現實中的物理層面,而無法察覺那主觀的核心──他人內在的心靈海洋。就是「你地圖」讓我們能夠有同理心。基本上,芭芭拉的腦部創傷為她創造了一個沒有第七感的世界。她有感覺跟思緒,但她無法藉由心智運作為自己描繪出這些訊號。即使當她說她「失去靈魂」時,她的用語有種僅止於描述事實的平淡特質,比較像是科學觀察,而非表達內心感受到的自我身分認同。(我當時很不解她的自我觀察與情緒為何可以如此互不相關。直到後來,我從較新近的研究中發現,描繪心靈地圖的大腦部位,跟我們觀察和評論自我特質的大腦部位,是截然不同的。這些自我特質包含了內向或焦慮等,或者就像芭芭拉所說的「靈魂」的特質。)
從我拿著芭芭拉的腦部掃描圖到圖書館找資料的那時開始,到現在這幾年為止,科學界對於前額葉皮質的連結功能有了更多的發現。例如,這個區域的側邊對於我們集中注意力有關鍵性的影響。它讓我們能夠把事情「放在心上」,並持續存在於意識中。而前額葉皮質的中央部位,也就是芭芭拉受傷的部位,則負責協調為數驚人的關鍵技巧,包括調節身體功能,與他人相互協調、平衡情緒、保持反應彈性、減緩恐懼,創造同理心、洞見、道德意識,以及直覺等。這些都是芭芭拉在與家人互動時,已經無法再運用的技巧。
我將會在後續詳述中央前額葉皮質的這九種功能。但即使只是現在簡短的說明,你應該也能看出,這些功能不但包含了調整心跳等身體功能,也包含了創造同理心與道德意識的人際功能,而這些都是健康的身心不可或缺的元素。
芭芭拉從昏迷中清醒後,她的腦傷似乎形成一個新的人格。她的一些日常習慣,例如飲食喜好以及日常衛生等習慣都跟以前一樣。她的大腦描繪這些基本行為的方式並沒有重大的改變。但是她思考、感受、行動,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方式卻徹底改變了。這影響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細節──包括琳娜歪七扭八的馬尾。芭芭拉依舊有基本的動作能力可以幫女兒綁頭髮,但是她已經不在乎綁得好不好了。
更重要的是,芭芭拉似乎失去了描繪心靈地圖最根本的能力,以致於她無法理解自己以及他人主觀內在的生命,也不在意其重要性。過去負責描繪第七感地圖的中央前額葉神經迴路現在已經亂成一團。中央前額葉的創傷也瓦解了芭芭拉與她家人的溝通──她再也無法發出或接收連結的訊號,從而參與她曾經最愛的人的內在心智世界。
班恩總結這些改變:「她已經不在了。現在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人,根本不是芭芭拉。」
身心健康的三角支柱:心智、大腦與人際關係
班恩過生日的那捲錄影帶展現了芭芭拉與琳娜之間充滿活力的溝通之舞。但是現在這舞蹈已經消失,再也沒有音樂的旋律,伴隨著兩顆心灌注到「我們」的意識中。當我們與他人內在的變化同頻率,他們也與我們同頻率,兩個世界才會融合在一起。藉由臉部表情與聲音語氣、姿勢與動作──有些是轉瞬即逝、十分細微的動作──而與別人產生「共鳴」。我們共同創造的整體確實會大於個人。當這種共鳴產生時,我們會感覺到生動的連結與活力。這就是兩個人心靈相遇時會有的情形。
我的一個病人曾經稱這種生動的連結是「感覺被別人感覺」:我們意識到別人分享了自己的內在世界,我們的心就在對方「裡面」。但是琳娜再也不能「被母親感覺」了。
芭芭拉面對家人的行為讓我想起一個親子溝通與依附的經典研究,稱為「無表情實驗」。這項實驗讓參與者跟旁觀者都覺得難受。
在實驗中,母親坐在她四個月大的寶寶對面,並在研究人員發出訊號時,停止跟她的孩子互動。這段不能跟孩子分享任何言語或非言語訊號的「無表情」階段,會讓人很痛苦。在最長不超過三分鐘的實驗時間裡,孩子會嘗試吸引此刻沒有任何反應的母親,期望與她親近。一開始,小孩子通常會增強自己的訊息,包括增加微笑、發出咕嚕聲以及眼神接觸等。但是在持續一段時間得不到反應後,她就會變得煩躁難過,原本爭取連結的一連串努力,此刻瓦解為痛苦跟憤怒。她甚至可能會把自己的手塞進嘴裡,或拉扯自己的衣服,試圖安撫自己。有時候研究人員或母親會在此時要求停止實驗,但是有時候實驗會繼續下去,直到嬰兒變得退縮、放棄,陷入抑鬱性憂鬱症的消沉崩潰中。這個抗議、自我安撫與絕望的過程,顯示了小孩子多麼需要父母給予他們同頻率的反應,來保持內在世界的平衡。
我們在出生時,大腦就已經被設定好要跟他人建立連結,而之後我們則藉由這種嬰兒與照顧者之間的親密互動,建立起腦中的神經網路,也就是自我意識的基礎。在生命最初的那幾年,這種人際協調是求生所不可或缺的,但我們終其一生都持續需要這樣的連結,才能維持身心健康與活力充沛的感覺。
琳娜曾經有一個與她頻率相同的母親。芭芭拉過去的生命形象已深深嵌在琳娜能創造第七感地圖的腦袋裡。但是芭芭拉卻已經無法描繪出琳娜的內心,她無法在心底感受她的孩子,無法再讓他們覺得「被感覺」。她對他們興趣缺缺,對他們的感覺與需要漠不關心,不再給予他們過去曾體會過的愛,這些都是這場內在悲劇顯現於外的跡象。
治療芭芭拉的家人讓我清楚看到,心智、大腦與人際關係,並非生命中可以各自分開的元素,而是構成健康的身心,缺一不可的三角支柱。即使琳娜已經七歲,但面對母親的毫無反應,最後也只能以沉默回應,因為這個支柱毀壞了。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