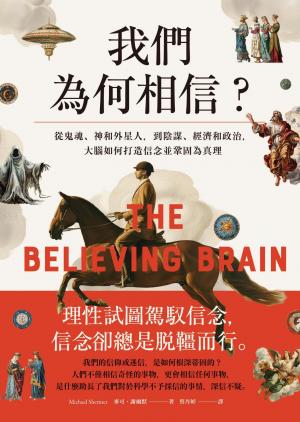那聲音清晰,傳達的信息更不容錯認。「奇克」埃米利奧.達皮諾(Emilio “Chick” D’Arpino)從床上跳起來,他驚訝地發現,在他耳中如此清楚的話語,居然不是房間裡有人說話。那是1966年2月11日凌晨4點,達皮諾獨自一人在臥室裡,剛聽到的聲音似乎沒有讓他感到不安。那聲音非男非女,儘管從來沒有類似經驗可供參考,但達皮諾就是知道,那聲音不屬於這個世界。
我在四十七歲生日那天認識了奇克達皮諾,那天是2001年9月8日,再三天就是那場震驚全球的災難,從此將歷史劃分為911前與911後。奇克想知道我願不願意寫一篇文章回答他的問題:是否可能得知在他處有沒有一個源頭,知道我們在這裡?
「呃,你是說上帝嗎?」我問道。
「不一定,」奇克回道。
「外星人?」
「也許,」奇克繼續說,「但我不想指明源頭的本質,重點是在他處,不在這裡。」
我心想,誰會問這種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奇克解釋說,他是一個家在矽谷的退休砌磚工,很喜歡追尋深層問題的答案,所以他會贊助鄰近的聖荷西州立大學和史丹福大學舉辦論文比賽和單日會議,以尋求答案。我從未聽說過有砌磚工贊助會議,這勾起了我的興趣,而且我向來敬佩自學者。
幾年下來,我和奇克成了好友,我越來越好奇,為什麼一個砌磚工會把微薄的家產,花在贊助探討人生大哉問的論文比賽和會議上。我有種感覺,奇克早就知道他問的問題的答案,但十年來不管我怎麼問他都避而不答。直到有一天,我又再一次追問,他才稍稍透露了一點:
我有過一次經驗。
經驗,很好!這種語言我很熟悉——信念系統的語言深植於經驗。什麼樣的經驗?
奇克又閉緊嘴巴了,但我還是不死心地旁敲側擊,繼續追問細節,什麼時候的事?
1966年。
在幾點發生的?
早上4點。
你看到還是聽到了什麼?
我不想談這件事。
但如果這次經驗這麼深刻,讓你到現在都還在追尋這些大哉問,那一定也值得和他人分享吧。
不,這很私密。
得了,奇克,我都認識你十年了,我們可是最好的朋友,我真的很好奇。
好吧,是一個聲音。
一個聲音,嗯。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麥可——你寫的那些關於幻聽、清醒夢和鬼壓床的文章我都看過了,但我的情況絕不是這些。那很清楚、明白、不容錯認,絕對不是出自我的心智,而是來自外面的源頭。
終於有點進展了,這個人是我結識多年的好友,平常看起來很理智,聰明才智也不在話下,我需要知道更多細節。在哪裡發生的?
在我妹妹家。
你怎麼會睡在你妹妹家?
我和老婆分了,正要離婚。
啊哈,是吧,離婚的壓力。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心理醫生跟你想的一樣——是壓力引發這次經驗。
精神科醫生?一個砌磚工怎麼會去看精神科醫生?
這個嘛,是特勤局(Secret Service)要我去安格紐斯州立醫院(Agnews State Hospital)找這個精神科醫生。
什麼?!特勤局?你為什麼會跟特勤局扯上關係?
我想跟總統談話。
好,讓我想想……1966年……是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越戰反戰……示威……建築工人想見總統……精神病院。對一個以研究信念為職業的人來說,這個故事太有趣了,所以我繼續追問。
你為什麼想要見總統?
把那個聲音源頭的訊息轉達給他。
什麼訊息?
這個我永遠不會告訴你,麥可——我沒告訴過任何人,我會把它帶進墳墓裡,我連我的小孩都沒講。
哇,一定是很重大的訊息,就像摩西在山頂從耶和華那裡領受十誡一樣。應該持續了一段時間吧,有多久?
不到一分鐘。
不到一分鐘?
是十三個字。
你還記得那十三個字嗎?
當然!
好啦,奇克,告訴我是什麼啦。
不行。
你有寫在某個地方嗎?
沒有。
我可以猜猜訊息的主題嗎?
好啊,你猜吧。
愛。
麥可!沒錯!一點也沒錯,愛,那源頭不僅知道我們在這裡,他還愛我們,我們可以和他建立關係。
源頭
我很想知道1966年2月那天早上,我的朋友奇克達皮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那次經驗如何深遠地改變了他的人生。我想知道奇克發生了什麼事,是因為我想知道當我們所有人形成信念時發生了什麼事。
以奇克來說,他的經驗是發生在與妻小分離的期間。分離的細節不重要(而且他也想保護家人的隱私),但分離的影響力很重要。「我那時候完全崩潰了,」奇克告訴我,[1]「在你能想得到的方面我都是崩潰的:財務、身體、情緒、心理。」
直到現在奇克仍然堅持,他經驗到的絕對不是出自他的心智。我強烈懷疑這一點,所以以下是我的解讀。獨自躺在床上的奇克醒了,也許正為又要開始煎熬的一天而憂慮著。心愛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邊,奇克對之後的人生感到徬徨,不知何去何從,更懷疑自己是否被愛。只要是經歷過愛卻不得回報的苦、關係不確定的焦躁、婚姻不順遂的折磨或是離婚那種痛徹心肺的淒涼的人,應該都很清楚這種攪動情緒渣滓的痛苦騷動——胃部翻騰、心跳加速、壓力荷爾蒙讓戰或逃的情緒激升——尤其是在帶來救贖希望的太陽還未升起的黎明前時刻。
我也體會過這種情緒,所以也許我是在投射。我父母在我四歲時離異,雖然那些分離和紛擾的細節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模糊不清,但有一個回憶格外清晰,當時不知有多少個深夜和清晨,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卻有種近乎眩暈的感覺,自己正在螺旋下降、縮進床裡,而我所在的房間不斷地向四面擴張,讓我覺得自己越來越渺小,既擔心又害怕……嗯……一切,尤其是關於被愛。雖然很幸運地,那種不斷縮小的經驗已經不再出現,但直到現在,還是有太多個深夜和清晨,失去愛的焦慮會再度襲來,如果是在其他時刻,我會用建設性的工作或體能活動去排除這些情緒,有時候會成功,但不是每次都有效。
接下來發生在奇克身上的事情,可以用超現實、空靈和超脫塵世來形容。1966年2月的那個清晨,一個安詳舒緩的聲音,平靜地傳達了我所想像一個在混亂中精神崩潰的人渴望聽到的信息:
你被一個更高的源頭所愛,他也希望你報之以愛。
我不知道奇克達皮諾聽到的是不是這些字,畢竟他還是不肯說,不過他多透露了一點:
那是關於源頭和我之間的愛,源頭點明了他和我的關係,以及我和他的關係,重點是——愛。如果非要說是關於什麼,那就是我們對彼此的互愛,我和源頭,源頭和我。
要如何理解超自然事件,並得出自然的解釋?這是達皮諾先生的兩難。
我就沒有陷入這種兩難,因為我不相信有超脫塵世的力量。奇克的經驗是由(我合理推斷出的)因果場景所引發,那個外部聲音其實來自他的內心。因為大腦無法察覺自身或其內部運作,而且我們一般的經驗都是來自外界的刺激經由感官進入大腦,所以一旦神經網路出錯或傳送訊息到腦部其他區域,而被當成外界刺激接收,大腦自然會將這些內部活動解讀成外在現象。這種情況既能自然發生,也能人為引發——很多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包括壓力)都會經歷幻聽和幻視,有大量研究(之後我會再詳述)指出,人為觸發這種虛幻的短暫現象有多麼容易。
不管這個聲音的實際源頭是什麼,一個人在有過這種經驗後會怎麼做?奇克說起了之後的故事,而這是我聽過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了。
那天是星期五,隔週的星期一——我記得是情人節——我就去了聖克拉拉郵局(Santa Clara Post Office),因為那時候FBI是在那裡。我想見總統,把我聽到的訊息轉達給他,但我不知道要怎麼才能見到總統。我想說可以從FBI那裡著手,所以我就走進去,告訴他們我想做什麼,然後他們就問我,「那麼達皮諾先生,你為什麼想要見總統?你是要抗議什麼嗎?」我說,「不是的,探員先生,我有好消息!」
你有仔細想過要怎麼告訴總統嗎?
沒有,我不知道要說什麼,我覺得到時候就知道了。基本上,我是想告訴總統「外面有一個源頭知道我們在這裡,那個源頭很關心我們。」
FBI探員有什麼反應?
他說:「這麼說吧,如果是這種事,你應該要找特勤局,他們才是直接面對總統的人。」所以我就問他,我要怎麼去特勤局?他看了看錶,然後說,「達皮諾先生,你先開車到舊金山的聯邦大樓,特勤局辦公室就在六樓。如果你現在動身,不塞車的話,應該可以在他們下班前抵達。」所以我就這麼做了!我坐上車,開到舊金山,找到聯邦大樓,坐電梯,結果特勤局辦公室真的在六樓!
他們讓你進去了嗎?
是啊,我見到了一個探員,他大概一百八十三公分高,我跟他說我想見總統。他立刻問我:「達皮諾先生,是總統有危險嗎?」我說:「就我所知是沒有。」然後他給了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電話號碼,他說:「這樣啊,那這個給你,你可以打給華盛頓特區的白宮總機,找預約秘書看你能不能預約時間見總統,這樣就可以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居然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就開始打電話,打了又打,打了又打,永遠打不通。這下我又卡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我是海軍退伍,所以我就去了退伍軍人醫院(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跟他們說了一遍我目前所做的事。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們都勸我別異想天開。「達皮諾先生,你為什麼想要見總統呢?」然後他們就請我離開,這時候FBI的人提到的那些示威者給了我靈感,我就在退伍軍人醫院坐下來不走了!
靜坐示威!
對,然後院方人員就說:「好了,達皮諾先生,你不走的話我就要叫警察了,我不想這麼做,你看起來是個好人。」所以我就跟那個人拉鋸了好一陣子,我記得他叫馬西,因為跟我女兒的名字同音。五個小時後他回來說:「你還在這裡啊,達皮諾先生?」我說:「對,我就待在這裡不走了。」他說:「真是的,達皮諾先生,你再不走我真的要叫警察了。」我說:「馬西,你做你認為對的事吧,我就待在這裡不走。」
所以他就報警了,後來來了兩個警察,他們問說:「有什麼問題?」馬西回答說:「這個人想見總統。」其中一個警察說:「達皮諾先生,你不能待在這裡,這裡是政府機構,服務老兵的。」我說:「我是老兵。」他說:「這樣啊……」然後他問馬西:「他有造成什麼麻煩嗎?有不當舉止嗎?」馬西說:「沒有,警察先生,他只是坐在這裡。」然後警察就跟他說:「這不歸我管。」他們討論了一陣子以後,就決定帶我去安格紐斯州立醫院,找能幫助我的人。
你可以想像得到,我走進一間州立精神病院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一開始他們和我談了一會兒,看出來我沒瘋也沒有精神病,其中一名警察就送我回我車上,他說:「好了,達皮諾先生,這是你的鑰匙,只要你保證以後不會再吵著要見總統,你就可以回家了。」但我還是堅持要見總統,所以他們就說要把我留院觀察七十二個小時。那是我最大的錯誤,我以為只要我想隨時都能離開,我錯了。
你在精神病院待了三天?你做了什麼事?
他們派了好幾個精神科醫師來和我談話,他們認定我需要更多觀察,而且要在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和兩名醫院指定的精神科醫師面前出庭,以判定我是否需要在精神病院住更久。2月24日那天,我站在法官和兩名精神科醫師面前,他們問了我一些問題,然後建議我住院。診斷:精神病。時間:待定。
聽到這裡,我的腦海已經浮現改編自肯.凱西(Ken Kesey)著名小說的奧斯卡金像獎電影中,傑克.尼克遜(Jack Nicholson)飾演的蘭道.麥克墨菲和露易絲.佛萊徹(Louise Fletcher)飾演的護士長拉契特,針對病人權益不斷過招的場景。我也把這個畫面告訴了奇克。
才不是!《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跟那地方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那裡真的很難熬。整整一年半,我只能坐在病房裡做他們交代的小任務,還要參加團體治療,和精神科醫生談話。
我們該怎麼看這件事?奇克達皮諾是脫離現實的瘋子嗎?有被害妄想症的瘋子?不是的。一段三十秒的經驗不會導致精神病,更不用說他一生都在書籍、會議和大學課程中追尋科學、神學和哲學,以期更瞭解自己和人類的處境。奇克也許是有一點野心過大,但他不是瘋子。也許他曾經因為環境壓力,而暫時脫離了現實。也許,至少我懷疑是這樣……或之類的。然而,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經歷過離婚帶來的情感壓力,他們卻沒有這麼離奇的遭遇。
或許是環境壓力加上大腦異常短路的結果——例如隨機神經元放電,也可能是輕微的顳葉癲癇發作,有許多紀錄指出,顳葉癲癇發作會導致幻聽和幻視以及過激的宗教行為。或者,也有可能是不明原因引發的幻聽。我們甚至可以乾脆把這歸因到大數法則;在美國,即使只有百萬分之一機率的事件,每天也會發生三百次——只要有足夠多的大腦在足夠長的時間內與環境互動,就算是特殊事件也不免變得常見了。而且因為人類的選擇性記憶,我們只會記住異常事件,而忘記平淡無奇的日常。
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憑空聽到聲音或看見異象,但我們和那些能憑空聽到聲音、看到異象的人的大腦,都是以相同的神經化學方式連接,從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到聖女貞德、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和大衛.考雷什(David Koresh)【2】都一樣。大腦如何形成信念,並根據信念採取行動的模式,才是這裡要探討的重點,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無可避免、不可抗拒、無庸置疑。信念是大腦創造的。無論奇克達皮諾發生了什麼事,我更感興趣的是,一旦我們形成了信念系統,又決心遵循時,信念系統就會支配我們,任何類型的信念都是如此:個人、宗教、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社會或文化。或是精神病…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