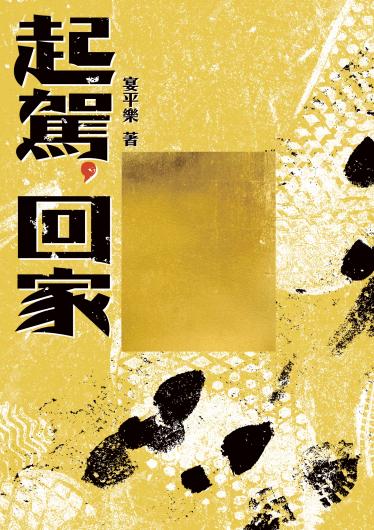鎮瀾宮
鎮瀾宮內被擠得水洩不通。各家媒體一大清早就提前來廟裡卡位,架高的腳架、充滿電力的電池;廟埕外面,各處宮廟、陣頭紛紛集結,有的王爺,大旗、鑼鼓開場,八家將踩著三步懺,威風八面的穿過順天路,頭旗踩著七星步,宛如掃開幽冥兩岸。

隨香旗一支接著一支售出,各家商鋪的老闆紛紛在旗子上幫人們寫上地址、姓名,掛上紅繩,綁好鎮瀾宮的平安符,象徵彷彿過海關的大印落下,在那紅、黃兩色的隨香旗上面印上了朱紅的力量。
為隨香客提供的素食點心攤,宛如流水席般鋪開,雖然歷年來陣頭團都有「點心不上桌」的慣例,但是因應時代的進步,特地擺開了朱紅色的桌子,彷彿象徵著和過去做一場世代的交替。準備來賺外快的小吃攤販,從順天路一直蔓延到大甲溪橋兩邊,隨著太陽越往西斜,人潮不僅沒有散去的跡象,甚至越來熱鬧,各家媒體爭相報導,新聞紛紛上線。
金寶珍銀樓裡,七十五歲的老闆金大成坐在躺椅上,任由電視畫面播送,吹著已經為銀樓服務了十年的大同電風扇打盹,不管門外吉普車上的大鼓陣多認真努力地打出沉重的聲音,新式的電音陣頭在長輩眼中不入流的粉墨登場,對他老人家來說就像兩個世界。
或許有些人覺得這是一生可以參加一次的媽祖遶境,但是對這裡的居民來說,這就是每年一度的日常。然而這種人擠人的場面,根本不會因為時間長短而消化,要一直等到子時,媽祖婆起駕後,緩慢地擠過大甲「水尾橋」後才會稍稍緩解。
金寶珍銀樓外。黑面拉動槍機,並且將一把仿製的九○手槍交給蔡正國。蔡正國拉起了黑色的領巾,兩人壓低帽子,走進銀樓。
「放炮喔!」
路上某家陣頭團的班主大喊一聲後,點燃地上的鞭炮,頓時間人潮走避。炮聲連天,炸開的紅紙宛如秋天落下的楓紅,燦爛又奪目,活力四射、載歌載舞。
只是金寶珍銀樓外,金順炷一開門就看到兩個蒙面歹徒,正一盤又一盤的將他家的金子往包包裡裝,而他的父親就被綑在椅子上。
金順炷急得退出門外,按下警鈴並且把大門鎖上,銀樓裡警鈴大作,蔡正國瘋狂衝撞大門。金順炷同時按下鐵捲門,想把門放下來讓歹徒鎖死在銀樓內。
葉成新怒了。他推開蔡正國,手槍對準玻璃門,然後藉著門外的鑼鼓喧天,肆無忌憚的擊發。
「嘩啦!」玻璃門碎裂。
蔡正國抓起裝滿金飾的包包跟葉成新衝出銀樓,連拉鍊都來不及拉上的背包裡,甩出來的金項鍊,一條要價都是五位數起跳。一出門外,葉成新毫不猶豫直接對著金順炷開槍。
「磅!」
金順炷倒下去的時候,蔡正國抱著頭,不可置信的看著葉成新──就應了阿仁的話,黑面這個人偷不到就搶、搶不到就殺。
不講道義,不想跟他來往。葉成新一把將蔡正國手裡的包包搶過來,蔡正國沒講話,只是看著葉成新的槍口對準了自己,然後他轉身拔腿就跑。
銀樓裡,看著自己的兒子倒在血泊中的老人家,落下淚,眼神中充滿了希望蔡正國救救他兒子的期盼。然而警鈴聲宛如蔡正國的喪鐘。他也轉身,扔下奄奄一息的金順炷,此刻的他只想逃得遠遠的。
香火袋
傳統的三合院,很多人家裡的大灶早就已經敲掉,就好像這整個世代,越來越快速,工業發展越來越興盛,傳統的農業漸漸沒落;本來每個家庭賴以為生的灶,一個一個走進了被淘汰的命運,敲成了一堆殘磚敗瓦,然後扔進鰲峰山或者大甲溪,替代成瓦斯鋼瓶。大街小巷,家家戶戶都有一個這樣的鋼瓶。瓦斯業者騎著野狼一二五載運著,彷彿不把灶敲掉就是跟不上時代; 宛如一個等死的幕垂老人,與那些扔進灶中的乾木柴一樣,發出對時代的悲鳴聲。
然而陳肇仁家的灶還沒敲掉。因為他是一個念舊的人。他總記得小時候,因為喜歡透過紅磚的縫隙看著灶裡高溫燃燒的柴火,甚至有好幾次想伸手去摸,李貴桃越說不可以摸,陳肇仁就越想去試試看。
最後父親看不下去了,抓著陳肇仁的手就往那滾燙的灶上小鐵門碰下去。雖然只有一瞬間,但是陳肇仁被燙得哇哇大叫。
李貴桃趕快過來抱著他,並且抱怨天底下哪有這麼狠心的父親。但是陳錦郎板起臉,嚴肅的告訴李貴桃,「痛一次,就知道那裡不能碰。」
小時的陳肇仁不懂,有好長一段時間看到父親都害怕得遠遠躲開。直到後來時代變了,看著那空蕩蕩的灶,三合院不用再燒火了,只是父親的生命也像這灶一樣,走到了盡頭。
陳肇仁不願意把這個灶敲掉,在上面擺了一個非常矛盾的現代化瓦斯爐。
安裝的師傅曾好心問他要不要把灶敲掉,現在他們公司安裝瓦斯爐只要加錢,就可以免費幫客戶移除舊灶,並且把磚頭運走。
陳肇仁拒絕了。不管外面時代怎麼改變,變得有多進步、多快速,或許這裡畢竟是鄉下的緣故,沒有受到這麼多的資訊影響,所以人心還可以保有一塊淨土,聽著灶裡嗶嗶剝剝的燒柴聲,歲月、靜好。
李貴桃把瓦斯爐移去旁邊,掀開灶上的鍋蓋,熱氣蒸騰而出;儘管有瓦斯爐,但是對於一些傳統食物,李貴桃還是堅持用大灶蒸。很多人問她為什麼這樣做?李貴桃總是說,用灶蒸的比較有味道;至於是什麼味道?她說不上來,也沒有人說的上來,只是既然她堅持,陳肇仁也不會多說什麼,更何況,李貴桃用大灶蒸出來的食物格外好吃。
好比說這一籠的粽子。桌上擺了滿滿的食物,神明廳的桌上,一支隨香旗被壽金夾住,橫放在陳家祖先牌位旁邊,旗子前面的小香爐插上三炷香。這隨香旗是新的,今天早上,李貴桃趕了一個大早去鎮瀾宮買的,綁了已過火的平安符,就等陳肇仁出發的時候,親自去媽祖廟跟媽祖婆「起馬」。
「起馬」的意思,是每個隨香客要出發前,都會拿著隨香旗到媽祖廟前,跟媽祖婆說,這段時間要跟隨媽祖婆往嘉義遶境,並且要先出發了,請媽祖婆保佑這一路平安。說完以後,旗子要過火,完成這道手續就可以出發上路。
神明桌旁邊,斗笠、袖套、背包、睡袋一應俱全,陳肇仁把這些東西全往「手推車」裡塞。這台手推車其實就是一台送瓦斯的推車,李貴桃吃了秤砣鐵了心,今年一定要陳肇仁去遶境,所以早請鐵工廠的師傅幫這手推車加上一個前輪,希望能幫陳肇仁減輕一些負擔,也不用扛著背包增加負擔。

八天七夜,勢在必行。
「你為什麼不跟土豆一起去?」王秀娟站在陳肇仁身旁,不開心的說著。
陳肇仁沒有回應她,只是低頭繼續收拾行李。
王秀娟:「你回答我啊。」
陳肇仁:「麥亂啦。」
王秀娟:「沒義氣。」
陳肇仁:「他叫我去我不去就是沒義氣,那我叫他不要去,他怎麼不聽我的。」
這時候,廚房傳來李貴桃的聲音:「阿仁啊。」
李貴桃從廚房走出來,王秀娟趕快把抓著陳肇仁的手鬆開。
王秀娟:「阿嬸。」
李貴桃點點頭,拉著陳肇仁的手:「粽好了,來吃一吃就去起馬,再來三天要食菜。」
李貴桃拉著陳肇仁要進廚房,但是陳肇仁抓著背包,眼神裡還有著猶豫。
王秀娟看著他,透著不甘心。
大大的花布圓桌,碗公裡放兩顆素粽,在暈黃的燈光下,熱氣蒸騰著。
王秀娟走進廚房小聲地對他說:「你不去他會死啦。」
李貴桃不高興的把手上的筷子,往桌上一拍。
「啪!」
陳肇仁跟王秀娟都嚇了一跳。李貴桃站起來,盛了一碗湯遞給陳肇仁:「喝湯啦。」
王秀娟把心一橫,伸手將脖子上的護身符拿出來,那是一個紅色的香火袋,上面繡了關聖帝君。是阿仁跟土豆結拜時候的那一個,他們倆人,一人一個。
王秀娟把香火袋塞進陳肇仁手裡:「你們結拜的捏。」看著這香火袋,陳肇仁緊握著拳頭,咬著牙突然轉身。
陳肇仁:「媽,我先出去一下。」
李貴桃喊著:「阿仁!」
陳肇仁才剛剛走出三合院外,就看到一個人從遠方跌跌撞撞地跑過來。不只他愣住了,連跟在他後面衝出門的王秀娟和李貴桃都愣住了。
因為這人正是土豆,蔡正國。蔡正國倉皇地摔倒在陳肇仁面前,葉成新給他的那把仿製九○手槍還掉在地上。
陳肇仁回頭看了李貴桃一眼,連忙把蔡正國扶起來,也不管母親有沒有看到,趕快將槍塞回蔡正國的褲子裡。
陳肇仁:「怎麼樣了?」
蔡正國:「幹,給我躲一下、給我躲一下,賊頭在抓。」
陳肇仁豎起耳朵,聽到遠處傳來的警笛聲,忽遠忽近的,在這寧靜的鄉下,好像地府裡面傳出來的索命聲音。這個聲音對於一般人來說,行得正、坐得直,不怕被找上門。晚上聽到這聲音,有時候反而是一種安心的保證,就好像有人隨時守著這一方小村莊的老百姓;但是對於做了虧心事的人來說,這聲音無疑是把他們躡手躡腳壯起的膽子打回原形,讓他們表面上看起來體面的生活,打回下水溝裡去當一隻過街老鼠,骯髒的蟲子。
李貴桃把臉別開,看都不想看蔡正國一眼。她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沒好事,因為這個魚寮裡,這種事情、這種神情,天天都有人在上演。王秀娟則是趕快抱著蔡正國,他們兩個用祈求的眼神看著陳肇仁。 警笛聲由遠而近,來到了三合院外面,閃爍的紅白色巡邏燈已經照得牆角邊、草叢間到處都是。
警笛聲關了,兩名員警下車,蔡正國緊緊抓著陳肇仁的手。他們兩個是結拜兄弟,他相信陳肇仁會救他,他們兩個可是拜過二爺的換帖兄弟。如果陳肇仁沒有一個豪氣干雲的父親,如果陳肇仁稍微自私一點,或許他就會直接把蔡正國給交出去。
偏偏他的身體裡留著陳家的血液。那一年陳錦郎在這個三合院的廣場,吆喝著十個兄弟結拜,歃血為盟、斬了雞頭,村子裡的年輕人無不羨慕他們十個,那種鐵血一般的義氣,今生求都求不來的情感。哪怕是親兄弟,都沒有那一天他們所流露出來的熱血與連結。
但是諷刺的是,這種一時無兩的意氣風發也就只存在那一天。那一天之後,某個兄弟搞上了另一個兄弟的妻子;某個兄弟為了簽大家樂,跟另一個兄弟翻臉;某個兄弟在某個兄弟的賭場欠下一屁股債,然後跑路到東南亞去了。
十個兄弟,分崩離析,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短短幾年,當年的歃血為盟,剩下唏噓;只有陳錦郎跟蔡成雄,他們兩個號稱肝膽相照。
直到陳錦郎遠洋漁船回來。這小漁村靠海,人的習性也跟海一樣,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必須要說前些年如果不是蔡成雄,陳肇仁沒辦法長這麼大。
十個兄弟,剩下兩個。
所以陳錦郎打從心底感謝蔡成雄,直到他跟陳錦郎借了一筆錢,陳錦郎把自己遠洋漁船賺來的錢幾乎都借給了他,而他卻跑了之後,李貴桃以為自己跟蔡家可以再無瓜葛。
但是這小漁村就這丁點大。陳肇仁長大了,沒人敢欺負陳家了,偏偏陳肇仁卻跟蔡正國也結拜做了兄弟。
陳肇仁衝進屋子,抓起斗笠、袖套、背包,直接幫蔡正國戴上。
蔡正國訝異地問:「這是?」
兩名員警剛好走進三合院。
「阿嬸,有看到一個年輕人跑到這裡來嗎?」
沉默,是人最習慣的應對方式。通常不回應,就可以不讓人感受到自己的情緒,而且也不做出錯誤的判斷。
所以當員警問出這句話的時候,李貴桃選擇什麼都不想說,王秀娟則是緊張得躲到蔡正國身後。
晚風徐徐吹過,四月的夜,春寒陡峭。白天的溫暖到了晚上,溫度會快速下降,彷彿是冬天仍在眷戀著不願意離開,奮起最後一絲力量,驅逐白天春暖花開的餘威。
淡淡的夜來香初開,空氣中飄著那幽靜的氣味。不知道是誰家的花香越過了低矮的圍牆,在空氣中除了一抹緊張之外,添上一縷淡雅。
這小魚寮,矮牆本來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我家的芭樂樹長到你家,芭樂熟成落在你家院子裡,這顆芭樂要算誰的?如果什麼都要計較個輸贏,那歲月哪有太平。
離家的遊子都說這裡的海風黏人,總讓人在春暖花開的季節。媽祖大轎被高舉的時候,記得回家看看;滿天的燦爛煙火,總會有一朵照映到你的家鄉。
陳肇仁主動迎向那兩名員警。
「大人,我們是準備要去跟大甲媽的啦,是怎麼了嗎?」
「這麼年輕就要去跟大甲媽,這麼誠心喔?」
陳肇仁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母親,母子連心。
從小,陳肇仁有什麼鬼點子,不用說話,一個眼神,李貴桃就知道這小鬼又想搞什麼花招,就像這時候一樣。儘管她完全不想接這題,但是想到過去的歲月,想到亡故的丈夫、跑路的蔡成雄。
李貴桃還是開口了:「我們這個細漢不好養,有跟媽祖婆說,如果養得大要去跟祂往嘉義遶境啦,今年剛滿十八歲啦。」
「咦,阿嬸,我欸記著妳不是只有一個?」年長的員警突然問,並且同打量陳肇仁跟蔡正國。
李貴桃指了一下阿仁:「嘿啦,沒這麼好福氣,這個我的啦。」
兩名員警同時把目光看向蔡正國。蔡正國一手拉著阿娟,一手緊緊握著懷中的仿製九○。
雖然不確定金順炷是死是活,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被抓,這關進去判個十幾年應該是跑不掉了。他不想被抓,也不想跟王秀娟的父親一樣;何況金子都被黑面拿走了,槍也是黑面開的,他卻要被抓,這太不公平了。
就在這時候,李貴桃淡淡地補上一句:「啊他們是結拜兄弟啦,這個也是我看著長大的,跟親生的一樣。」
「喔,安內喔。」比較年長的員警笑著拍拍蔡正國的肩膀:「這麼年輕就這麼誠心,很好捏,廟埕已經很多人了,有去起馬了嗎?」
「還、還沒啦。」蔡正國有點結結巴巴的回應。
老員警用手比劃了兩下:「這樣趕快去,現在廟埕人已經很多了,可能擠不進去,但是在外面跟媽祖婆講一下還是要的。」
聽到老員警這樣講,年輕的員警趕快壓低聲音說著:「學長,但是剛剛那個人很可疑,明明是跑到這邊來啊。」
老員警還沒說話,李貴桃已經指著敞開的三合院大門:「唉唷,大人如果不放心,不然進來喝茶啦,看要找人我們也可以幫忙找啊。」
「無啦,我們還有代誌要忙,也不要耽誤阿嬸的時間啦。」老員警馬上把帽子戴好,回頭瞪了年輕的員警一眼:「阿嬸說沒看到就是沒看到,難道會騙我們嗎?」
李貴桃只是笑著。年輕的員警盯著蔡正國,儘管心裡有諸多疑惑,但仍只能摸摸鼻子讓老員警給拉上警車離開。
鬆了一口氣的眾人,就像剛打完一場仗似的虛脫,蔡正國把斗笠拿下來塞給陳肇仁,轉頭就要離開,但是陳肇仁抓住他的手臂。
陳肇仁:「你要做什麼?」
蔡正國:「跑路啊。」
陳肇仁:「要跑去哪?」
蔡正國:「反正沒你的事。」
陳肇仁:「外面都是警察,你出去就一定被抓!」
蔡正國:「不然我現在要怎麼辦!」
陳肇仁:「跟我去嘉義。」
蔡正國:「你白癡喔,我是你兄弟,但是…」
蔡正國頓了一下,斜眼瞄了李貴桃一眼,李貴桃不高興的轉身進屋子。
蔡正國才接下去說:「但是我不是你媽的兒子,不用陪你演戲啦。」
陳肇仁:「不是要你演戲,你走到彰化,可以去郭溝仔找昌叔。」
本來打算離開的蔡正國,緩緩把手放下。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