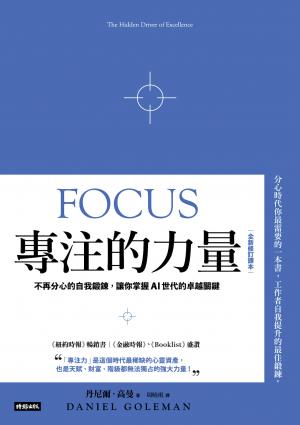柏格(John Berger)是曼哈頓上東區某家百貨公司一樓的便衣警衛。柏格監視購物人群的行為,正是「注意力」(attention)的鮮活寫照。他身著不起眼的黑色西裝、白襯衫與紅領帶,手持對講機。柏格從不停下腳步,他的專注力永遠落在熙熙攘攘的購物者身上。你也可以說,他是這個賣場的眼睛。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一樓的賣場都有五十位以上的購物者,他們流連在各個珠寶與名牌服飾專櫃之間,看看范倫鐵諾(Valentino)的圍巾、掂掂普拉達(Prada)的皮包。他們瀏覽商品的同時,柏格也在瀏覽他們。
柏格在購物人群中來回穿梭,有如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一般看似毫無章法地移動。幾秒鐘前,他還站在皮包專櫃後方緊盯著一名可疑人士;轉眼間,他已經移到門口的有利位置,以便仔細觀察那令他起疑的三人組。顧客的眼中只有商品,渾然不覺此時此刻,柏格銳利而警覺的眼神沒放過他們任何一人。
印度有句諺語:「當扒手遇見聖人時,扒手眼中還是只有口袋。」而在熙攘人潮中,柏格眼中看見的只有扒手。他的目光就像一只探照燈般來回掃射。你可以想像他的五官變形幻化為一個巨大的眼球,彷彿希臘神話中的獨眼巨人。柏格就是專注力的化身。他的眼睛在掃描什麼?「他們目光移動的方式或身體的動作。」柏格說,這些會洩露他們偷竊的意圖。例如好幾個人聚在一處,或一個人獨自鬼鬼祟祟地四處張望。「我在這行幹太久了,那些訊號一看就知道。」
當柏格專注於五十位購物者中的某一人身上時,他能夠設法忽視其他四十九人,以及其他任何事物──在令人分心的花花世界中,心無旁騖是一種高超的本領。
這種縱觀全局的覺察,與等待罕見訊號出現的持續警惕狀態,二者的交替運作需要許多不同類型的「注意力」──持續的注意力(sustained attention)、警覺性、目標定向,以及同時掌握以上各項的能力──每一種都是不可或缺的心智工具,皆以迥然不同的大腦迴路為基礎。
柏格能夠持續地搜尋罕見的狀況,這也是專注力的各層面中,最早開始科學研究的項目。二次大戰期間,由於軍方需要雷達觀測人員長時間維持高度警覺性,因此催生了一項加強維持警覺性的研究分析。這項研究發現,因為注意力延滯的緣故,人員在值班時段的尾聲會錯過較多訊號。
在冷戰達到高峰時,我曾拜訪一位受五角大廈委任的研究員,他的任務是研究在剝奪睡眠連續三到五天(這是他們估計若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軍官在碉堡深處必須保持清醒的時間)之後,人們警覺性程度的變化情形。所幸他的實驗從未有機會應用在現實中,但這項研究仍有振奮人心的發現―只要動機夠強,人們即使缺乏睡眠三天以上,還是能保持敏銳的注意力(反之,如果他們漠不關心,就會立刻昏昏欲睡)。
直到近幾年,研究「注意力」的科學開始百家爭鳴,其範圍已遠遠超出對警覺性的研究。這門科學告訴我們,注意力的技巧高低足以決定我們從事任何工作的優劣。如果注意力受阻,我們的表現就會十分差勁;但若充分發揮,則能出類拔萃。人類的敏捷機智所仰賴的,就是這項微妙的稟賦。雖然注意力與卓越表現之間的關聯,歷年來鮮為人知,其影響卻擴及幾乎每一件我們想完成的事情。
有多到數不清的心智活動都和這項靈活的工具密不可分,其中幾個基本項目,包括理解、記憶、學習、感知我們如何與為何有某種感覺、察覺他人的情緒,並圓融地與他人互動。揭示這項肉眼看不見的有效性因素,能讓我們更清楚看到增進此種微妙稟賦的效益,同時也更了解該如何著手。
我們往往會透過心中幻想出來的畫面,清楚地意識到注意力的最終產品──我們的主意是好是壞、一個意味深長的眨眼或邀請式的笑容、晨間咖啡散發的香氣。然而,我們卻沒有注意到「覺察」本身發出的光芒。
注意力(無論哪一種形式)是鮮為人知且不受重視的心智資產,但對於我們如何掌控人生的方向卻至關重大。在此,我的目標是讓人們注意到這種難以捉摸、未獲賞識的心智能力,並明白它是我們大腦活動與實現美滿人生的關鍵角色。
我們的旅程將從探討注意力的一些基本性質開始;柏格所展現出的高度警覺性僅是其中之一。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於此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包括專注力(concentration)、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開放覺知(open awareness),以及大腦是如何指引注意力對內監督與管理心智活動。
如上所述,許多重要的能力是建立在我們心智生活的這些基本機制之上。其中一項是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這種能力可以培養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接著是同理心(empathy),也就是人際關係技巧的基礎。這些都是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簡稱EQ)的根本。如同我們後續將會探討到的,缺乏這類能力足以破壞一個人的一生或事業;若使這類能力變得強大,則能使一個人更有成就、更成功。
除此之外,系統科學(systems science)將引領我們走向層面更廣的專注力,也就是我們和周遭世界的關係。這些複雜的系統界定且限制了我們的世界,而專注力可以調整我們的腳步,讓我們更能適應。2當我們對這些重要的系統進行調整時,此種對外的專注力面臨著潛藏的挑戰:我們的大腦並不是為了這項任務而設計的,因此我們總是茫然失措。但是,系統意識(systems awareness)有助於我們了解整個組織、經濟體的運作方式,也能了解滋養著地球上萬千生命的全球進程。
這一切可歸納為三大類:對內(inner)、對他人(other)與對外(outer)的專注力。若要擁有美好的生活,我們必須在各個面向都保持靈敏度。有一個關於注意力的好消息,來自神經科學的實驗室與學校的教室:人們發現了強化這條重要的「心智肌肉」的方法。注意力的運作方式很像肌肉──用得不好就會萎縮,使用得當就會成長。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一些聰明的方法是如何進一步開發與鍛鍊注意力的「肌肉」,甚至修復欠缺專注力的大腦。
領導者若想成功,便需要這三種專注力,缺一不可。對內的專注力,可以讓我們在直覺、價值觀以及較佳的決策之間順利協調;對他人的專注力,可以使我們的人際關係和諧;對外的專注力,可以引領我們在更寬廣的世界中走往正確的方向。當領導者與其內心世界失調,將失去方向感;當領導者無視於他人,將變得蒙昧無知;當領導者對外部世界的運作漠不關心,將受到出其不意的打擊與挫敗。
此外,不只是領導人能從這三種專注力的平衡中獲益。我們所有人都處於這種艱鉅的環境中,面對著現代生活的緊張、競爭性的目標與誘惑。這三種專注力的每一種,都能幫助我們找到平衡,讓我們感到快樂,同時具備生產力。
注意力(attention)一詞來自拉丁文的「attendere」,原意是向外延伸,將我們與世界相連接,進而塑造與定義我們的經驗。認知神經學家麥可.波斯納(Michael Posner)與瑪麗.羅斯柏(Mary Rothbart)寫道,注意力所提供的機制是我們「覺知這個世界、自願規範我們的思想及感覺之基礎。」
安妮.崔思曼(Anne Treisman)是此研究領域的大學學院院長,她指出,我們如何運用我們的注意力,決定了我們所見。或如電影《星際大戰》所說的:「你所專注的重心,決定了你的現實。」
▌瀕危的人性時刻
一對母女正搭乘渡輪前往某個度假小島,一路上小女孩緊緊摟著母親,頭只搆得著母親的腰,而這位母親卻沒有什麼反應,甚至似乎根本沒注意到──因為她一直全神貫注於手中的iPad。
沒過多久,同樣的情景再度上演。我與九位週末結伴出遊的姐妹會的女學生共乘一輛小巴士,她們在昏暗的巴士裡分別坐定,不到幾分鐘,每個人都拿出iPhone 或平板電腦,微弱的螢幕餘光在車廂裡閃爍。在她們傳訊息、滑臉書之餘,偶爾也會蹦出幾句對話,但巴士裡多數時間都一片沉默。
那位母親的冷淡與九位姐妹會成員間的沉默,都體現出科技是如何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也擾亂了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二○○六年,一個新字「pizzled」進入了我們的字典;這個字是「困惑」(puzzled)與「生氣」(pissed)的組合。當隨行相伴的人忽然拿出手機、開始與別人談話,「pizzled」就是用來形容你此時的感受。過去,人們在這種時候會感到受傷、氣憤,現在反倒成為生活的常態。
帶我們走向未來的領導者──青少年──則是這種大變動的震央。二○一○年代初期,他們平均每月發送的文字訊息暴增至三千四百一十七則,比數年前足足增加一倍。同一時期內,他們講電話的時間大幅減少。目前美國青少年平均每天送出超過一百則文字訊息,相當於他們清醒時平均每小時發送十則訊息。我還親眼見過一個年輕人一邊騎單車,一邊打字發訊息。
一位朋友描述:「最近我去拜訪紐澤西州的表親與他們的孩子,這些孩子擁有人類已知的所有電子玩意兒。從頭到尾我只能看見他們的頭頂。他們一直在看iPhone,看別人傳來的訊息、看臉書上有什麼新動態,不然就是沉迷在電玩遊戲中。他們渾然不知周遭發生了什麼事,也沒辦法與人進行比較長時間的互動。」
現在的孩子在一個全新的現實環境中成長,比起真人,他們更親近機器,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情況。這造成了不少問題,原因之一是,孩子大腦中的社會與情緒神經迴路,是透過一整天下來與他人的接觸及對話來學習。這些互動會塑造大腦神經迴路;與人們接觸的時間愈短──同時眼睛盯著數位螢幕的時間愈長──意味著他們愈欠缺學習。
所有數位化的活動,都是以減少與真人面對面的時間為代價,然而,與人互動是我們學習「非語言」(nonverbal)溝通的媒介。這幫生長於數位世界的新人類可能十分嫻熟鍵盤操作,但他們解讀面對面的行為時卻可能笨拙無比──尤其無法感覺到當他們中斷對話去看手機訊息時,對方將感到多麼沮喪。
一位大學生觀察到,生活在一個充滿推文、更新動態、「發布我今天晚餐的照片」的虛擬世界裡,會產生孤獨與隔離感。他發現同學們喪失了對話能力,更別說是那種能豐富大學生活的、發人深省的討論。他還說,就因為要讓那些數位世界的朋友可以立刻知道你玩得有多開心,「不管是生日、演唱會、朋友出遊或派對,如果你沒有撥些時間自正在從事的活動中抽離,就無法從這些活動中得到樂趣。」
再說到注意力的本質,注意力是一條認知上的「肌肉」,讓我們能夠看完一則故事、堅持一項任務,以及學習與創造。正如本書後續將提到的,年輕人永無休止地盯著電子產品的那些時間,在某些層面上可能有助於他們獲得某些認知技能。但與此同時,是否也會導致他們欠缺核心的心理技能?因此,不免仍存在擔憂和疑問。
一位八年級的中學老師告訴我,她多年來都會指導班上學生閱讀伊迪絲.漢彌敦(Edith Hamilton)的《希臘羅馬神話》(Mythology)。以往她的學生都很喜愛這本書──直到五年前左右。她告訴我:「我開始看到孩子們不再那麼興奮,甚至連成績最好的學生都不愛讀這本書。他們說閱讀這本書太難了、句子太複雜,要花好長的時間才能讀完一頁。」
她懷疑,或許學生習慣了簡短零碎的簡訊文字,因此閱讀能力已經大打折扣。有位學生向她坦承,說他過去一年來花了兩千個小時在電玩遊戲上。她補充道:「當你要與《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競爭時,教學生文法規則是很困難的。」
就極端的案例而言,在台灣、南韓與其他亞洲國家所出現的青年網路成癮──電玩遊戲、社群媒體、虛擬實境―已被視為全國性的健康危機,使年輕人陷於孤立。美國八歲至十八歲的電玩遊戲玩家中,有八%似乎符合精神病學對上癮的診斷標準。大腦研究顯示,當他們玩遊戲時,他們的神經獎勵系統(neural reward system)出現的變化,與酗酒者和藥物濫用者十分類似。偶爾會聽說這樣的恐怖個案:成癮的遊戲玩家白天睡覺、晚上通宵玩遊戲,幾乎不吃飯也不洗澡。如果家人嘗試阻止,他們甚至會暴力相向。
和諧融洽的關係需要注意力的投注──相互對等的專注。我們每天都航行在充斥各種分心事物的汪洋大海中,因此,致力於擁有人與人之間的寶貴片刻,已成為我們前所未有的使命。
▌注意力的匱乏
接著,我們要談到成年人注意力下降的代價。墨西哥一位為大型電台工作的廣告業務抱怨:「幾年前你還能為廣告商製作五分鐘的展示影片,如今必須縮短至一分半鐘──如果屆時還無法抓住他們的注意力,每個人都會開始看手機訊息。」
一位教電影的大學教授告訴我,他正在閱讀他心目中的英雄──法國傳奇導演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自傳。但他發現:「我沒辦法一口氣讀完兩頁以上。我會有種衝動,想要上線去看是否收到新郵件。我認為自己正喪失持續專注在任何正經事的能力。」
由於無法抗拒檢查電子郵件或臉書的衝動,因而不能專注於與我們談話的人身上;大師級的社會互動觀察家暨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稱這種情形為「飄離」(away)的姿態,彷彿在告訴他人,「我對於此處正在進行之事不感興趣」。
讓我們回溯至二○○五年的第三屆全數位(All Things Digital)會議,主辦單位將大廳的Wi-Fi 斷線,因為觀眾忙著用筆記型電腦,沒有注意台上的活動。觀眾飄離了,陷入某位與會人士所形容的「持續性的局部關注」(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來自講者、周遭其他人,以及他們正在筆電上進行之事的過量訊息載入,所導致的心智模糊(mental blurriness)狀態。為了對抗現今的這種局部關注,矽谷某些公司已經禁止在會議中使用筆電、手機與其他電子工具。
一位出版公司的主管承認,要是一陣子沒檢查手機,她會有「煩躁感。你會想念發現有一條新訊息的感覺。你知道與別人談話時不該看手機,但這會上癮。」因此她與丈夫約法三章:「當我們下班回家後,手機必須擺進抽屜裡。如果手機就在眼前,我會坐立難安,我就是必須看一下。但現在我們試著更融入彼此的當下,我們會交談。」
無論對內或對外,我們的專注力會持續地對抗分心。問題在於,我們的分心使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一位金融業的主管告訴我:「當我在會議中注意到我的心思已不知跑到何方時,就會懷疑我在當下究竟錯失了哪些機會。」
我認識的某位醫生表示, 已經不只一位病患告訴他,他們會用注意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簡稱ADD)或猝睡症的藥物「自我治療」,以跟上工作進度。有位律師告訴他:「如果不吃這個藥,我就無法閱讀合約。」過去,病人需要醫師診斷才能取得處方,但現在這些藥物已成為日常的提升表現用藥。有愈來愈多青少年偽裝注意力缺失的症狀,以獲得興奮劑的處方,用化學方法來取得注意力。
專門指導領袖如何自我管理精力的顧問東尼.史瓦茲(Tony Schwartz)告訴我:「我們的工作是讓人們更了解該如何使用專注力──目前他們的專注力全都很糟。專注力如今已成為我們客戶心中的頭號課題。」
接收過多資訊的壓力會導致人們敷衍了事,例如只看標題來過濾電子郵件、跳過大部分語音留言、草草瀏覽訊息與備忘錄。這裡的問題不只是我們養成的注意力習慣讓我們更沒效率,而是訊息量也已多到讓我們沒時間去思考其真正含義。
所有這類問題其實早已有人預見。時間回到一九七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司馬賀(Herbert Simon)在文章中談到即將來臨的資訊世界,他當時就已經提出警告,資訊消耗的是「接收資訊者的注意力,因此,資訊的富足會導致注意力的匱乏」。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