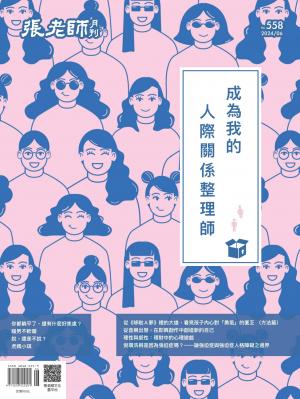課業與社團活動失衡的小佑 小佑升上高中之後,非常喜歡社團裡新鮮的人事物,假日也經常投入大小社團活動中,從不缺席。爸媽覺得以前小佑很宅,現在能走出去多交朋友滿好的。 但兩次段考後,爸媽發現小佑經常要三催四請才能完成課業,或壓線繳交作業。在家裡多數時間都盯著手機,小佑說社團或課業小組報告真的有事需要溝通討論,但爸媽卻發現他多半在聊天。此外,段考表現也無法再維持國中的中上水準,爸媽若多關心他的課業,小佑就會有滿大的情緒。 到了下學期,小佑幾次補習開始遲到,理由是社團練習耽擱,爸媽只是稍微提醒小佑,但後來甚至有一次根本沒到!小佑解釋是因為社課成果要驗收了,得加緊練習不能影響同組的夥伴。「高中生就應該以課業為先,根本就本末倒置了!」爸爸簡直氣炸,嚴厲地訓斥小佑。小佑覺得爸媽不理解社團活動對他的重要性,也認為爸媽並不支持他去做真正有成就感的事情,似乎在他們眼裡只有課業才是要緊事,心裡很是委屈不平。 失去重心與連結的「躺平」狀態 寒假期間,小佑幾乎跟社團同學在一起,也辦了一些跨校活動,他成為幾個學校間的風雲人物,手機整天有回不完的訊息。下學期開始,小佑因為手機使用太晚,上學經常出現遲到的狀況。導師表示小佑的作業、成績狀況都沒有改善,甚至出現了在課堂上趴睡的狀況,但中午跟放學時卻都精神奕奕地去參加社團活動。導師試著關心小佑,但冷淡應付的反應加上屢勸不聽,導師沒輒地表示希望爸媽對小佑多加管教約束。在第一次段考後,媽媽和小佑因為成績的事情嚴重地爭執,決定在下次段考成績有起色前,禁止小佑再參加社團活動,並且嚴格要求門禁。 自從那次衝突後,小佑起初還會去社團串門子,但是跟不上大家練習進度後,成果發表或是和外校的聯合社課也就沒有機會與舞臺了,這對小佑來說非常失落,去了也是觸景傷情,漸漸地常在社團聯課時翹課去打球,課後也幾乎不去補習班,去也是趴睡。課堂上亦經常一副精神萎靡的樣子,導師的形容是「眼神空洞,沒有目標與動力學習」。小佑也抗拒去輔導室找老師晤談,覺得自己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爸媽!應該是他們去接受輔導。 小佑也不太願意向其他同學談到自己的狀況,更覺得自己成績、社團都失利有點面子掛不住,開始對很多事情都顯得不在乎、漫不經心的樣子。有一回因為小佑對小組報告不上心,同學忍無可忍地在書面報告上就沒列小佑的名字,這讓小佑很生氣覺得不被尊重,言語衝突後,便較少在班上說話,上課也多半戴耳機聽自己的音樂、看自己的小說或趴著睡覺。 小佑頓失生活重心後,多數時間都專注在手遊和網路交友上。班上雖然也有些同學玩同款手遊稍有話題聊,但格格不入的感覺讓小佑愈來愈不喜歡上學。 躺平後的消極放棄與衝突 高一下學期的重頭戲,對一些學生來說是能否當選社團幹部,對其他學生來說是選班群(以前稱選組)。小佑也不例外,他很希望自己先前在社團的投入與表現能被學長姐看重,但因為下學期的參與狀況並不理想,最終沒有被選為任何幹部,小佑非常失落,甚至很生氣,覺得自己過去的努力被否定了。 「反正你這學期也沒有認真參與社團,沒被選上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就專心在課業上嘛,這也不是什麼壞事啊!」爸媽這麼回應。小佑覺得爸媽根本不了解社團對自己的意義。 到了選班群時,爸媽對於小佑一直以來對生涯「沒有想法」很是擔憂,他們焦急地要求他參加補習班、學校的校系介紹講座,甚至是報名外面的營隊課程等,但小佑不是意興闌珊,就是在課程中也沒有太多的投入。在上網選填班群意向前一週,親子間爆發了很嚴重的衝突。 「我們已經給你所有的資源,哪有高中生像你這麼消極的,連自己的未來都不想一想,社團對你的未來有什麼幫助?我們不會一直供你啃老喔⋯⋯你還是選○○班群好了啦,這對你將來更有利⋯⋯」爸媽急切地唸叨著。 「我的未來是我自己的事,用不著你們管,你們哪時候聽過我的意見了,我想要的你們從來都不會支持,我為什麼要聽你們的!?」小佑氣急敗壞地回應著。雙方你來我往,僵持不下。 「躺平」是長期的挫折與氣餒造成的狀態 近年來,「躺平」這個詞彙常成為討論焦點,然而,是否該將這些不想(放棄)努力、你說了算、與我無關等消極的狀態,視為不思上進、挫折容忍力很低的表現呢?或許我們應該先試著理解這些「躺平」背後的意義。 以小佑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思考:從國中階段到會考前,有沒有人陪他聊過他對高中生活的想像或期待?上高中可能面對到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有哪些可能的挑戰?讀高中對他個人來說的意義是什麼?甚至是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遇到挑戰時,師長是否能夠扮演支持、傾聽、對話的角色,幫助他有勇氣嘗試新事物,而非僅僅給指導和建議。 個體心理學家阿弗列德.阿德勒認為,周遭的他人如何看待孩子以及他正在面對的挑戰,都會影響孩子「如何應對生命挑戰」的態度與信念。 假若一直以來自己的聲音始終都會被師長的意見或其他人的經驗取代,其實那是在對孩子明示、暗示著「我們不信任你做得到」,漸漸地孩子也就覺得自己的想法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壓抑自己的聲音,變得退縮,不再表達自己的想法。這裡有個重要的提醒:即便孩子終會因為自己的選擇遇到困難和挫折,但那都是重要且不可取代、很珍貴的學習。師長的角色不應是再補一刀「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說過了」,懲罰與落井下石從來都無法帶來我們預期的效果,而只有不斷地給予孩子鼓勵與支持,一起討論接下來怎麼做會更好,才能激發出孩子面對生活挑戰的勇氣。 陪伴與安頓焦慮,帶來起身的動力 沒有人天生就只想躺平,阿德勒也認為生命的挑戰雖然會讓人感到挫折與自卑,但我們天生就有克服和超越自卑的傾向。在諮商實務中,的確看到許多類似「躺平」的孩子,他們的生命經驗中多有不斷被貶抑自尊的情況。唯有當孩子感受到「你的意見是重要的」、「你的想法是值得被聽見的」、「你可以去嘗試看看」、「我相信你」時,才能讓氣餒到只想躺平的他們(也就是阿德勒所說自我跛足、表現無能)願意踏出那其實一點也不舒適的舒適圈。躺平其實不舒服,因為在表面看似無所謂的消極樣態下,內在是焦慮不安甚至情緒可能是憂鬱低迷的。 我們可以回歸小佑對高中生活的期望,而非師長的期待,陪著他整理幾個月經歷的種種事件和情緒,一起思考以下問題: 1. 什麼是目前比較急迫要處理的呢(現實考量)?例如,或許可暫時就他能勝任的學科表現來做選班群的思考,高二再思考學期結束時,是否要轉換班群。 2. 什麼是小佑最在意的事情呢(目標與需求)?也許社團幹部並不是最大的致命傷,而是社團、班上都失去了人際的連結,讓小佑覺得上學沒有什麼意義跟動力,怎麼一點一滴地重建人際連結便是重要的討論。 3. 什麼是比較可能開始調整的呢(做得到的累積成就感)?例如,高二重新分班,小佑也有機會建立新的人際關係,他希望自己以什麼面貌示人呢?在新學期開始前的兩、三個月,也許先把本學期有個收尾,好好調整自己的作息與心情就很已經很不容易了,行有餘力再來想想高二社團的選擇對他的影響。 然而,每個人總會有那麼些時刻想要躺平、暫緩、休息一下,這是很正常的,我們也要允許孩子、允許自己擁有這個空間,這個空間能讓我們透過自我調適達到復原,釐清一些生活的問題,也不致超過我們的心理負載。想要讓躺平的人起身,毋須找方法讓他起身,而是讓他自己願意、想要起身,理解、陪伴與鼓勵始終是最佳的動力來源!
林上能
諮商心理師,從教職出走到社區,執業於點亮心燈心理諮商所,專注於阿德勒取向心理諮商、生涯諮商、督導工作,並投入心理健康政策倡議。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