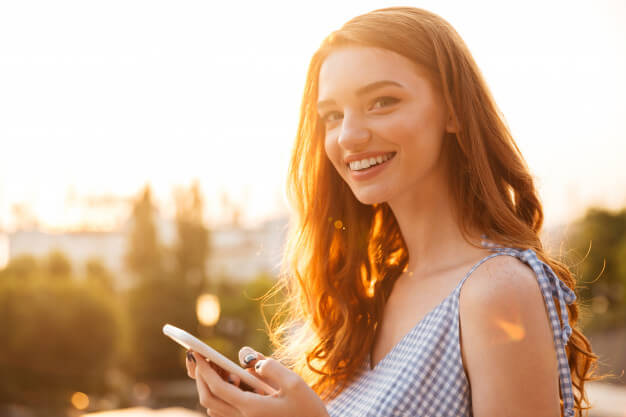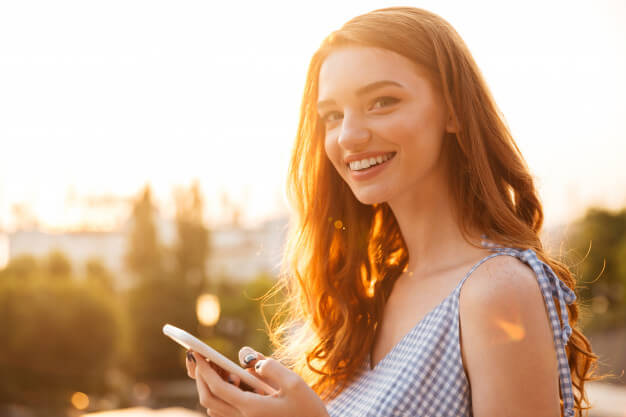生活是首影像詩
妳如果以規格化的美與笑容,爬進了別人的鏡子裡,就出不來了,妳將成為她或他顧影自憐的目標。
我記得我高中時期,隔壁的書局除了參考書外,最多的就是偶像卡。那時可以塞在錢包裡的小卡片都印上了偶像巧笑倩兮的照片,供人隨身與平安符放在一起。當時無論東區還是萬年都充滿這樣的小店。
遠看有上百張的圖片,裡面的女生都溫柔淺笑,像是一致約定好的:「我們女孩要療癒這世界喔!」店裡一整個牆壁都是女生的笑容。
如今想來滿壯觀的,只是現在移到了個人的手機桌面,或很像電影《藍色恐懼》裡的粉絲一打開電腦,他偶像大同小異的笑容就彈跳出來,滿螢幕的普普式開罐笑容,頓時有幾分驚悚。
90年代,人們都稱那些女孩們為療癒系偶像。這種事事過境遷也就忘了,直到日本女星竹內結子死時,人們在塗鴉牆上追憶的仍是她各種包容的笑容,如聖母般可原諒一切;舒緩男性焦慮。但我始終想起的是她在日劇《神探夏洛克》與《草莓之夜》那英姿颯爽的酷樣,我那時想,這位從《七夜怪談》系列就開始演戲的實力派,終於有不笑的自由了。
是的,但連死去時,人們追憶的都還是她溫婉一笑。讓我想起不只一次看到她習慣掩飾悲傷的報導,裡面寫著她不讓自己哭出聲,需要大哭時,甚至會將毛巾塞在嘴巴裡,不讓周遭人發現
我常想,一個從小被關注到大的美女,到底有沒有關機或不癒療別人的資格。你或許會說,這是日本人特別壓抑,但韓國女星成排的笑容,大家如空氣般的習慣。
或許我們當年崇拜王菲不只是她的歌藝,而是她擁有了不笑的豁免權,就如同我們曾視不愛笑的楊乃文為女王般,一起隨歌名高呼她是「Queen」。
女生的笑,跟女生的大哭(如辛曉琪的〈領悟〉、楊貴媚《愛情萬歲》中的大哭)、婆媳劇中女人的歇斯底里。在90年代,這三樣是銷售利器,但如同鏡子破碎一般,莫名收集的是如此破碎的女性群像。
因此,當竹內結子自殺後,我掛懷的是,她是否終於可以關機了。美麗的女人被重播的總是那逐漸失去了真實線索的笑容。就像我在電影《逃亡的女人》裡看到的金敏喜,總是溫柔微笑地面對所有的人,想講的話卻欲言又止。她要逃掉的不是誰,而是她自己的假象。
就如同我也無法想像,如果林志玲不笑會怎樣。只有近年出來的少數少女如小松菜奈、9m88可以不笑。其餘的,連張曼玉都在得了影后後,才停止了早期發條式的笑容。
美女要依照他人的想像生存,看似簡單,但久了,就很像是靈魂被包了保鮮膜般透不了氣,裡面歪扭的難免長出枯枝與壞死。畢竟,完成別人的夢想並不一定是自己的夢想。
近來影集《后翼棄兵》很紅,下棋競賽題材原本就討喜、聰明又漂亮的女生討喜。女主角在孤絕生命裡打破自己又重建也夠吸引人。但乍看最有魅力的,卻是她那不笑的臉。當棋盤擺在她面前,有足夠自信的世界裡,她連笑的念頭都不需要有(對照她同鎮笑個不停的女生與她養母)。同時也很紅的《艾蜜莉在巴黎》則完全不一樣,後者依賴著她被點閱的假象,愈不安時,她愈笑。她的笑是眾人的安慰藥;她自己的鎮定劑。
而《后翼棄兵》的貝絲,沒有將自己的臉當公共財的概念,她擁有真實人生,不需要各種以假亂真來增值。貝絲從不知如何笑,到因真正感到自由而笑。
如果,我們可以摘掉女孩長期被暗示的面具,那何妨放那些曾被拘於滿牆的女人笑容,一點重開機的自由呢?
馬欣
作家、影評與樂評人。曾擔任金曲獎、金馬獎、金音獎評審、專職寫作,專欄文字散見於鏡周刊、娛樂重擊、博客來OKAPI、非常木蘭、自由時報、聯合報、端傳媒等,著有《反派的力量》《當代寂寞考》《長夜之光》《階級病院》。
閱讀完整內容
本文摘錄自
女生的笑到底是療癒自己還是他人?
Marie Claire美麗佳人
2020/第332期
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