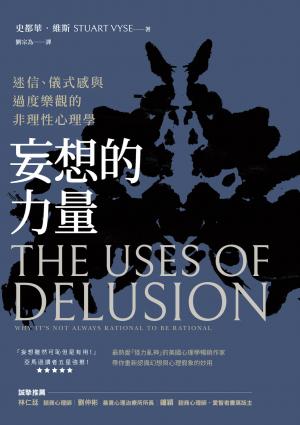一九七二年,我剛開始攻讀研究所,而有位朋友死於車禍。他是越戰老兵,離開戰場回到家鄉後,生活就陷入困境。某個深夜,他妻子蘇珊在睡覺時,他的車子意外撞上了幾公里外的一棵大樹。
後來的幾個星期裡,我們一群人花了很多時間陪伴蘇珊,帶她出門散心,甚至把她灌醉。我們每個人都會抽空陪伴著她、抱抱她,不讓她獨自一人。
蘇珊在大學裡的圖書館工作。她的辦公桌位在七樓的窗戶邊,丈夫過世前,她每天工作結束時,都會看到丈夫走到圖書館接她下班。每天從窗戶看到丈夫的身影,蘇珊就知道要收拾東西下班了。
丈夫去世幾個月後,某天晚上蘇珊告訴我,她每天仍會在工作快結束時低頭望向街道,期待看到他走向圖書館。這不僅是個習慣。她不願意接受事實:好不容易熬過戰爭、平安返家,卻不知何故就消失不見了。
「我常感覺到他正要走進家門。」蘇珊說道。
有些時候,生活中需要一點妄想,特別是面對親友的死亡。美國作家瓊.蒂蒂安(Joan Didion)在自己的回憶錄《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中,寫下了丈夫突然去世後的哀悼歷程:
表面上看起來,大多數時候我都是理性的。外人看來,我好像完全明白死亡是不可逆的。我授權法醫解剖屍體,也安排好了火葬事宜。我計劃好要將他的骨灰帶去聖約翰大教堂。1
蒂蒂安堅持,丈夫去世後的第一個晚上她要獨自度過:「這樣他可能就會回來了。」2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蒂蒂安的生活重心只有一件事:等丈夫回來。所以他的鞋子都還在鞋櫃裡,他回來時用得到。
對我來說,在人類所有的特徵裡,最可愛的就是會做出自相矛盾的行為。毫無疑問地,人類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智慧的物種,然而,正常的人平均每一個小時,就會做出一件明知道不該去做的事情。有些人會執著於錯誤的想法,並提出貌似合理的理由。通常,我們都能意識到自己的不一致之處:「我知道不應該這樣做,但我克制不了自己,我就是想做。」說起來令人羨慕,動物就沒有這種矛盾心情。貓狗有時會做瘋狂的事情,但牠們的信念非常單純,不會去懷疑自己的行為是錯的。
這本書會談到人類行為上的許多矛盾。我們所堅持的信念和所採取的行動通常搭不起來,但這些矛盾很有價值,因為它們能幫助人們度過艱困的日子,掌握當下的生活情況,並實現個人目標。
我跟蒂蒂安一樣,基本上是理性主義者。我是行為科學家,專門研究迷信心理學和占星術。《懷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雜誌有我的專欄「行為與信仰」,而那本雜誌的基本精神是「科學和理性」。我的志業就是宣揚邏輯和證據的重要性,並強調它們是最重要的行動指標。這兩者是各種偉大成就的基礎,靠著它們,人類才能度過難關、生生不息。
但經過這麼多年來的探究,我對真理和謬誤的區分慢慢有所轉變。每個人都有偏見,也有迷信和不理性的一面,但它們都是瑕不掩瑜的特徵。在生活中,若想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就應該擺脫妄想,以理性主導自己的行為。然而,在生命中有些時刻,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拋棄自己的妄想。
有用的妄想並不少,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就像牙齒和骨骼,它們與感官上的幻覺很相似。圖1.1是著名的繆勒萊耶錯覺(Müller-Lyer illusion)。每一個修過通識心理學的人都能告訴你,這兩條線的長度是一樣的。我在電腦上畫出左邊的線,然後複製貼在右邊,所以它們的長度完全相同。不相信的話,你可以拿尺量量看。

儘管證據充足,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左邊的垂直線看起來就是比右邊的還要長。有一種解釋是,人們在生活中常常接觸到立方體,而左邊的圖形看起來像是稍遠的立方體內角(如牆角),而右邊的圖形看起來像是立方體的外角。最後,大腦會依據自己與遠處物體之間的距離去判斷它表面上看來的大小。因此,我們不會把一輛遠方迎面而來的汽車誤認為是玩具車。繆勒萊耶錯覺是源自於人類的深度知覺(depth perception),左邊的線看起來更長,因為它似乎距離我們比較遙遠。
但就算你實際去測量、知道這兩條線的長度一樣,也了解深度知覺的原理,也無法消除掉這項錯覺。它們看起來就是不一樣長。本書所談到的其他妄想也一樣難解;就算知道是自己誤信了,也無法擺脫,彷彿它們是人體的基本構造。
有些妄想比較鬆散,所以人們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屈從於它們。但妄想不同於感官的幻覺,前者會大大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雖然妄想聽起來不是好事,但有些確實會對生活有所幫助。
問題就出在人類太聰明了!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都指出,理性是人類的基本特徵,而其他物種沒有。只有人類才有完整的意識去欣賞和評論生活。存在主義哲學家(這些人老是悶悶不樂)認為,理性和對理解的渴望是人類獨有的重擔,而不可避免地,我們才因此認識到生命的荒謬和無意義。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法國作家卡繆說道:
如果我是森林裡的樹,或是野外的貓,這樣的生命也許還有意義,或者就沒有意義上的問題,因為我屬於這個世界。但透過我的人類意識,以及我對熟悉事物的信念,我變成了這廣大世界的對立者。這個荒謬的理性使我對立於一切創造物,再怎麼寫也無法跨越這一切。3
理性和大腦造就出了偉大的城市、藝術和科技。雖然我們沒有陷入卡繆對存在的絕望感,但也都了解,人類的智力並非毫無缺陷。此外,也只有人類會意識到,自己和所愛的人有天終將死去,而一棵樹或一隻貓是無法體會到人類面對生老病死的心境。
此外,人類不只有單一心智。從當前主流的認知理論看來,大腦同時有兩個獨立的主機板在運作;一個想得快,另一個想得慢。前者是系統一,也就是大腦快速而直觀的反應,它讓我們即時處理外在事務,而無需借助更強大的裝置。透過個人經歷和經驗法則,大能就能處理每天要接收的數十億位元的資訊量。相比之下,系統二是速度較慢的超級電腦,它能進行數學運算、弄清楚系統一做不到的事情。系統一習慣當機立斷、繼續前進;系統二則需要一點時間來權衡所有的利弊得失。你準備開車去旅行時,有條不紊的系統二會弄清楚,如何將家人的行李都裝進後車廂;而系統一會依據直覺來決定午餐要吃什麼。
兩個主機板同時處理資訊,當然優點很多,但也有缺點。過去四十年來的行為經濟學研究顯示,系統一與系統二常常會相互矛盾。心理學家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與已故的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獲得了二○○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作家麥克.劉易斯(Michael Lewis)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稱之為「橡皮擦計畫」。4在一系列簡單但巧妙的實驗中,康納曼和特沃斯基發現,快速行動的系統一大多能做出正確決定,但有時卻會犯下嚴重的錯誤,而這時就該馬上止血。
最經典狀況就是比例偏見,心理學家艾普斯坦(Seymour Epstein)以下例來說明。5實驗現場有一大一小兩個碗,只要能從中抽到紅色的果凍豆,就能贏得一百塊。小碗裡總共有十顆果凍豆,一個紅色,九個白色;而大碗裡總共有一百個豆子,十個紅豆和另外九十個白豆。擅長深思熟慮、進行數學思考的系統二會告訴我們,雖然只有一次抽獎機會,但這兩個碗抽中紅色的機率都一樣,所以不管挑哪個都沒差,擲硬幣決定就好。
但是,直觀的系統一令受試者遲疑,所以忍不住要看著大碗的十個果凍豆。其實他們並不覺得選哪個碗都沒差,反而認為大碗裡的紅豆看起來比較多。果然,艾普斯坦的學生有八成都選了大碗。
是的,系統一確實偏袒大碗,但這並沒有壞處,反正兩邊的獲勝機率是一樣的。當然這不是實驗的結果。研究人員接著從大碗中換掉一顆紅豆,以繼續測試系統一的比例偏見。
小碗還是一樣,十顆果凍豆中有一顆是紅色的;但在大碗的一百顆豆子中,紅色的只有九顆,白色的則有九十一顆。在系統二的推論下,選擇小碗的獲勝機率維持在一成,但選擇大碗的獲勝機率卻下降為百分之九。在抽獎前,實驗人員還提醒同學,大小碗的獲勝機率已經變不同了。但結果仍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同學選擇了大碗,儘管抽中的可能性較低。接下來,實驗人員再次降低大碗中的紅色豆數量,降到剩五個,也就是獲勝機率為百分之五,僅僅是小碗的一半。然而,還是有百分二十三的參與者選擇了大碗。6
現在你看到了衝突所在:直觀的系統一決定選擇大碗,而愛計算的系統二被冷落了。大碗的獲勝機率不到一成,應該選擇小碗才對!類似的情況很多,我們也有意識到這個矛盾,但做決定時還是會違背自己的最佳利益。直覺的力量實在太強大了,再怎麼聰明的人也不時會違背自己的判斷,做出有損自己利益的決定。
比例偏見是一種心理機制上的錯覺,類似於感知錯覺(如前述的繆勒萊耶錯覺)。但差別在於,繆勒萊耶錯覺無法改善,你明知道事實為何,但在視覺上還是會覺得左邊的更長。相較之下,比例偏見可透過自主性的選擇來修正,所以選擇大碗的人只是屈服於直覺。但只要有更多人運用講究理性的系統二,就能說服依賴系統一的人。總之,相較於感知上的錯覺,比例偏見等心理偏見比較好化解。
過去幾十年來,許多行為經濟學家跟心理學家都在研究這類問題。人類的思維中有各種偏見,當中有許多是導因於系統一和系統二的衝突。比例偏見的情況比較好解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正確的答案。當然,直覺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只是偶爾會讓我們選了錯誤的碗。心理學家都想弄清楚人性中的矛盾處,並將我們帶向較為正確的道路。
然而,這本書不是為了否定任何偏見或謬誤。相反地,我即將描述的人類特性,雖然自相矛盾,但最好要保留下來。我沒有要大家全然放棄理性、邏輯和知識,轉而只相信直覺和信仰。這絕對是不明智的。我只是想提出平衡的觀點:既然人類有高度的智慧與清晰的思維,那也一定會有理性所不及之處。現代人也越來越能接受,非理性是一種特徵,而不是缺點。直覺、猜測和幻想是天生的心理機制,有時會讓系統二感到困惑,但仍非常有用。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