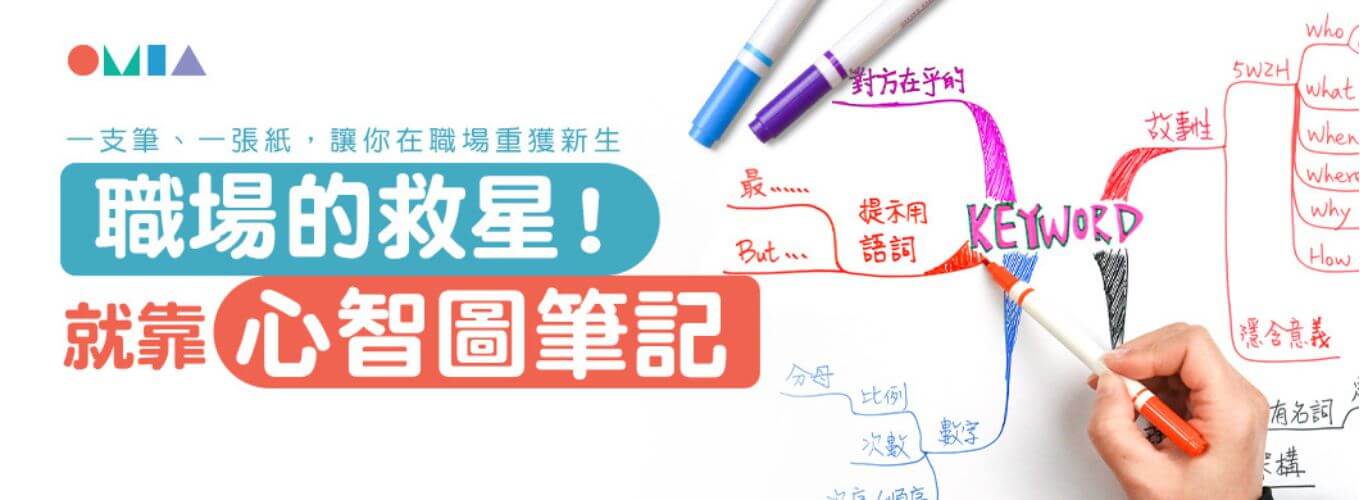談城鄉》田園浪漫背後的道德逼問
天空藍得讓你仰頭走路有酩酊感,空氣清澈得好像人活在透明裡。我的村莊山嫵媚、水純淨、人可愛,但是奇怪了,為什麼,村莊裡一半的人,注定要比我早死十年?
文/龍應台
我住在一個只有九百戶人家的村落,而且我的小家,距離九百戶人家聚集的一平方公里村落中心,還有四公里,四周沒有路燈,只有叢林環抱。
從半山上遙望下面村落的燈火,有一種明亮的溫暖感。有一天,在毫無目的地的遊蕩中,吉普車駛過乾涸小溪,進入一條不曾走過的山路。顯然人跡久不至,落葉腐木覆蓋,路面中央破裂成深溝。
緩慢行駛中,突然看見一隻巨大的鳥從路邊草叢啪啦啦振翅竄起;這龐大的猛禽,低低掠過我的車窗。牠的腳爪抓著一條垂下來長長的衣帶,是不是太重了,牠突然放鬆腳爪,竄進右邊的樹林,停在高枝上,俯視我。
我清晰看見猛禽黃色的爪子,和爪子上面鐵鉤似的黑色腳趾。
回頭仔細看那摔在地上的衣帶,竟然是一條大蛇,一公尺半長,和我的手腕一般粗。
等候片刻,確定那蛇不動了,我下車,想知道那是什麼蛇,蛇有多長。
靠近了才看見,無法知道蛇的長度,因為,可憐的南蛇,整個頭都被吃掉了,而且不知道被吃掉了多少。
大冠鷲還在樹上,盯著我的一舉一動,顯然在等我離開,好回來打包,帶食物去給孩子吃。
發動車,小心地避過南蛇,繼續這條荒野的路。雖然目睹血腥震動不已,心中卻充滿沉重的感恩。
沉重,因為知道這個地球已經不堪負荷,山林大火、洪水暴發、瘟疫蔓延、海水淹城,世紀末的景象觸目驚心;感恩,因為看見村落的外面,還有叢林野地,還有荒溪亂石,還有猛禽大蛇,讓我知道,我這個大腦發達、肢體孱弱而貪得無厭的動物,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臍帶,並沒有完全斷裂。
突然聽見激昂犬吠。一群飢餓得眼睛發綠光的遊蕩狗,有的已經瘦到露出一排一排突出的肋骨,正包圍著一隻落單的、瘦小的白鼻心。這是弱弱相殘。人,把狗帶到山林裡丟棄,讓他們因為饑餓而變成森林裡野生動物的殺手。
村落的意思,就是樹幹比電桿多,房舍比樹冠矮;看天空不必抬頭,因為天空藍得無邊無際就在眼眉之間,插花不必去花市買,因為路旁溪邊籬笆上,無處不是可插之繁花。
村落的意思,所有的比例都違反常規。
沿著山路開往村落,看出去,藍色的海,在綠色的小葉欖仁的頭上;五顏六色的公雞,大剌剌趴在空蕩蕩的路心,體積彷彿比狗還大。水牛悠悠走在村路上,老人的三輪電動車緩慢跟在牛屁股後面,看起來是牛在遛人。

▲【小檔案】
龍應台
現職/作家
著作/《野火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親愛的安德烈》、《目送》、《大武山下》等
村落的聲音,有時辰,有季節。破曉是公雞遠遠近近的啼叫,清晨是斑鳩的呼喚,傍晚,母山羌斥罵孩子怎麼還不回家的叫聲一聲比一聲急促,夜裡,黃角鴞和領角鴞的呼聲交織,從東邊的森林一路迴盪到西邊的山谷。
深夜裡,犬吠此起彼落。村子裡有一位醫師,照顧著全村的老人。醫師說,狗的夜哭,聽它從村裡東西南北哪個角落響起,他就會知道,今晚,哪個長輩,走了。一隻狗哭,全村的狗都開始悲泣,此起彼落,綿密連結,是一種靈魂的告慰。
春天,鄰居們用簡訊問候,「春天到了,他們都醒來了。要留意。」他們,指的是冬眠過後準備出來覓食的蛇們。
我們聽不到蛇的身體滑過草葉的聲音,但是五色鳥叫得囂張,山與山之間,整天都是他們瘋敲打鋼琴似的歌聲,斑鳩夾雜其間。然後蛙鳴愈來愈猖狂,蟋蟀加入伴奏,白頭翁和樹鵲在外圍鼓譟,如同交響樂的鋪陳,到盛夏一瞬間不可收拾如爆炸,以至於夏夜坐在庭院裡,無法交談,因為蟲魚鳥獸孤注一擲的生命歡唱,這時,密密織成一片穿腦魔音網。
這一切,到秋冬,彷彿有一個看不見的指揮,棒子一收,瞬間萬物寂然,葉子黃了,隨風而起。
村落裡生活的我,照顧十八隻母雞。雞舍的門,雖設而長開。雞姊妹們天一亮,就拍拍翅膀奔向草地,啄食蚯蚓蝸牛。太陽露出臉的時候,她們又紛紛回到自己的草窩生蛋,蛋一落地,就跳出來唱半分鐘「生蛋歌」。我從一百公尺外的書房,聽見那特殊的旋律,就知道,可以去取蛋了。早餐,就是荷包蛋。
村落人以物易物。大門外掛在樹上有一袋絲瓜,我收下絲瓜。哪天出門時,帶一盒雞蛋,開到他家大門,大門沒關,走進去,把雞蛋擱在陽台上。你給我絲瓜,我給你雞蛋,他給我香蕉,我給他蓮霧,今天收到酪梨,明天給他芒果。有一天,收到一隻大龍蝦,紙條寫「我兒子今天早上到海裡抓的」,我只好給他一本書。
山中遇猛禽叼蛇歸來,赴部落姊妹的約會。姊妹們都是阿美族,深目隆鼻,身材高䠷,是她們的特徵。部落的小酒吧只有四張桌子,都坐了客人。
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每個人和每個人都有點親戚關係。飲酒次數多了,誰和誰曾經愛上了誰、拋棄了誰、後來誰得報應死了,我也逐漸知道了。夜漸漸深,酒瓶愈來愈多。「給你取個阿美族名字吧?」七嘴八舌,她們開始討論起我的「氣質特徵」,然後為首的,很阿莎力地當場命名,「我們本來叫妳『姑娘』,妳就叫Kaying吧。」

▲從潮州到都蘭,從農業人文聚落到原住民曠野。蛇、雞、狗⋯⋯,都在提醒人與大自然難以切斷的臍帶。(龍應台提供)
那給我命名的姊妹,是我在部落小吃店認識的。有一天,我給自己帶了一個迷你瓶威士忌,準備獨酌。她端菜給我時,說了自己的名字,於是我說,「今天客人不多,妳坐下來跟我喝杯威士忌吧?」
她不屑地看了一眼桌上的迷你瓶,「不喝你們的威士忌。我有我的。」她當下從沾了油污的圍裙兜兜裡拿出一個小杯,然後從櫃檯取來一瓶高粱酒,「你喝我的酒。」
兩個陌生人,就在一個村落裡燈光萎靡的小店,喝起高粱酒。廚房裡做菜的、廚房外端菜的、坐在外面路邊塑膠矮椅駝著背正在剝筍的,還有這小吃店不在場的老闆娘,還有這隨身帶著高粱酒杯的,都是寡婦。
「年紀都不大,怎麼都是寡婦?男人怎麼了?」
她黯然。
全村的男人女人都到城市裡打工去了。中年回鄉的女人,很多是離了婚的,或者,不得不回來照顧孤苦老人。
「男人回村嗎?」
她爽快地仰頭大飲一口酒,笑了,「男人,抬著回來啦。」
她的笑,在小店慘白的燈光下,盡是黑色的陰影。
我很快就看到了一個「被抬回來」的男人。
跟著醫師去給一個病人送飯。一個中年男人,坐在輪椅上,垂著頭,幾乎全身癱瘓,只能伸出手臂把眼前的飯勉強送到嘴裡。屋子裡像個垃圾場,一群野貓,團團把他圍住,睜著大眼等候——如果他的手臂無力拿到便當,貓就會一擁而上。
男人在城市工地裡做模板工人,受了傷,被「抬回來」。兒子也在遙遠的城市裡求生存,他就一個人,一個半癱瘓的人,與野貓搶食。
狗沒食物,「愛」就別說了
二○二三年,我追蹤兩個法案,都和我美好的村莊有關。五月底,立法院會期結束,擱置了一個法案,通過了一個法案。
被擱置的是「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條文。這個擱置,意味著,你知不知道,村莊裡有一種狗,只有三條腿,而且到處都是。
鄉村裡很多人,把狗看作純粹工作的畜,讓牠們看守果園或農地。人不在場,狗是綁著的,而人往往忘記狗需要食物,需要水。狗需要「愛」,就別說了。
吉普車在村莊行走,看到太多沒水喝、沒食物吃的飢渴交迫的狗,看到太多三條腿的殘廢狗。一些鄉人放任自己的狗入山,而另一些鄉人又在山裡設金屬陷阱,狗一踏入,就得撕掉一條腿。
吉普車在山中行走,看見的,就是被人所棄置的狗——不僅只是個人,連地方政府,因為無力照顧流浪犬,會成批地棄置浪犬於山林,製造了數量龐大的遊蕩犬。本來應該被放在家中、抱在懷裡寵愛的狗狗,變成飢餓瘋狂、目露凶光的群獸,山裡的貓頭鷹、環頸雉、食蟹獴等等野生小動物,被這突然入侵的物種威脅到生存。
這個修正案,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又擱下了。
三讀通過的,則是討論了足足十年的「原住民族健康法」。
這個法的要求,其實非常謙遜,就只是要衛福部定期召開「原住民族健康政策會」,而政策會的成員,具原住民身分的人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由部長擔任召集人,就原住民族特殊健康問題、生活形態、環境、生物因子及醫療資源等等面向,定期調查與研究原住民族健康狀況及需求,並建置原住民族健康資料庫,培育原住民族健康照護人員。
原住民是國民,這不是本來就該做的事情,怎麼還需要特別立法?
我是台北市民,把我的平均餘命和部落裡與我喝酒的姊妹們,以及她們的男人,平均餘命放在一起看看吧。為什麼,身為台北市女性市民,我的生命會比山林裡的兄弟姊妹,多了幾乎十年?
村莊裡的原住民是如何死的呢?原住民的嬰兒死亡率是全體國民嬰兒死亡率的兩倍,山地原住民嬰兒死亡率更接近三倍。二○一九年的統計,原住民的幼年人口(一至十四歲),死因第一名是「事故傷害」;青壯年人口(十五至四十四歲)死因第一名也是「事故傷害」為首。
也就是說,從一歲到四十四歲的原住民,最常因為「事故傷害」而死*。怎麼會這樣呢?
來到村莊,我明白了。譬如說,很多村莊沒有自來水,村民依靠水管從山中接出山泉水。到山林中巡一次水管,就可能被毒蛇咬,毒蛇咬了要到醫院去注射血清,可能是四個小時的路程。他的命,等不了四個小時。
那個被貓搶食的中年男人,又是從北部哪個建築工地被抬回來的呢?

人類要怎麼不走上絕路?
村莊田園是浪漫美好的。我在緋紅色的晨曦和雞啼中醒來,拿一杯熱咖啡坐在我的中東海棗樹下,看絲綢般的白雲在山峰與山峰之間繚繞如煙;山峰與山峰之間,到了夜裡,滿布星斗。
台灣的村莊田園少不了原住民族。這份浪漫美好,有他們的份嗎?壽命差十年,我們怎麼面對這種道德逼問呢?村莊田園更少不了山中的猛禽野獸,也少不了陪伴人類的蟲魚鳥獸。這份浪漫美好,他們又付出了什麼代價?
一九七○年以來,人這個物種,已經消滅了六○%的野生脊椎動物、魚類、爬蟲類。人,要怎麼樣才不讓自己也走上絕路呢?
我的吉普車仍舊在山中、在海邊、在村落的裡面和外面行走。我深愛、深愛這裡的一切。
可是,我必須承認,我是不安的。■
*原民會「一○八年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
閱讀完整內容
本文摘錄自
龍應台:我那美好的村莊
天下雜誌
2023/6月 第775期
相關